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世界五百强中的一多半都在中国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合资或者独资。
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如何恰当地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成就?这种经济成就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与环境根源?未来二三十年的中国经济能否继续高速增长?我们还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问题一:如何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成就?
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过去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认识问题出现了认识上的飞跃,结果是中国的政府治理逐步走上了所谓良性治理的轨道。
目前国内外有关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功的理论和解释当中,不外乎“FDI(外商直接投资)或对外开放说”、“乡镇企业说”、“制度和产权说”、“合约和激励说”、“财政分权说”等等。笔者作为中国经济问题的一名研究者,看了这么多的古今中外文献,总感觉似乎大家都只说对了问题的一方面,而远没有说对全部。
就拿“FDI或者对外开放说”来说,对外开放的确很重要,它对于中国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中国企业、中国人开眼望世界上的确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也绝非对外开放一个因素就能圆满解释。
在这种成绩的背后一定有很多、很重要的故事要讲。比如,中国政府对于历史问题的清醒认识、政府管理体制的及时调整、经济发展理论认识的深化、前苏联东欧国家解体经验的深刻理解,这些难道不重要吗?想想看,如果没有政府包括全社会对这些重大问题认识的深化,哪来对外开放。退一步讲,如果没有这些认识的深化,仅仅打开国门就能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让我们再退回到历史上去看看。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朝代,它们对外开放的程度其实并不高,比如,两汉、隋、唐、明,清前期等,但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对他们取得的成绩而言,对外开放绝对不是主要的解释因素。
从经济理论看,对外开放对于小国经济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没有对外开放就难以分享规模经济、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好处,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对外开放的作用可能并没有日、韩、新加坡等小国那么大。
还有,对外开放即使很重要,但对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它的重要性和作用也是非常不同的。比如,对于当时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而言,它的确非常重要,但对已靠近世界技术前沿、发展前沿的国家而言,对外开放的作用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
拿美国来说,过去二十多年,其贸易依存度不超过30%,为什么这么发达的国家其贸易依存度却很低?一是,它已处于世界技术和创新前沿,对外开放是有选择性的开放,而不是全面开放;二是,美国的国家规模足够大,对外开放的作用可能并不是很大;三是,对外开放程度太大对于美国自身的发展并不一定有利,但对世界的影响却很大。
同样道理,对外开放对于三十年前的中国而言的确作用很大,但对于改革三十多年后的中国而言,它的重要性可能已经大大降低,相反,一个公平、贯通的一体化的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各国针对中国逐年上涨的贸易制裁和反倾销案件数量,我们也许就知道中国这个贸易大国对于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了。在目前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还像过去一样重视对外贸易,恐怕只会招致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贸易制裁和贸易保护。
从数据来看,过去三十多年,无论是吸引的FDI、进出口总额、GDP或者GNP,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寿命、国家的外汇储备、财政收入等等,我国都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如果我们分析对外贸易相关变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可能发现,这种影响是正向的、显著的。
但是如果就此认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完全就是对外开放却可能是十分错误的、危险的。因为对外开放在短期看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正在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下降;此外,我们如果过度强调对外开放,也可能会蒙蔽决策层的视线,并误导我们今后恰当合理地应对目前以及未来的各种挑战。同样道理,我们的以上说法也可以用来批驳其他各种单因素假说的解释力和重要性。
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过去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认识问题出现了认识上的飞跃,结果是中国的政府治理逐步走上了所谓良性治理的轨道。比如,中国政府对1840年以后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有了清醒的认识——关起门来搞发展可能行不通,对1912-1949年国民党脱离中国小农经济基础而采取西方一套政府管理体制并最终丢掉政权的深切体会,中国政府对计划经济时期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以及最终国民经济走向了破产边缘进行的深刻反思,特别是对苏联、东欧由于经济发展落伍最终导致国家政权发生巨变的事实进行的深刻反省,如此等等,都使得中国政府认识到了政府合宜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这些政策不管它是什么,因为改革之初中国政府可能并不知道它们具体是什么,在改革之前改革者的头脑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一揽子的政策和改革框架,相反,“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换句话说,不管什么样的政策和制度,只要是合宜的,适合于经济体的,为企业和大众所欢迎的,就是好的必要的政策。
其结果是,我们看到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1983年乡镇企业改革的推行,1986年城市金融、汇率、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1994年财政分权体制的改革,1998年以后房地产市场的放开,2002年西部开发,2006年新农村建设、2007年的科学发展观等等。
其实所有这些政策、改革或者发展战略都是中国政府治理逐步走向良性发展轨道的一个个轨迹和组成部分。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如此成功的关键,恐怕就在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与政府对改革的大力推动,其实完全可以称之为所谓的政府对于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等的一系列良性治理举措。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个问题,恐怕就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清楚地认识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很好地尊重了中国适合小农经济的地理和环境条件,并且通过渐进、试错的方式逐步找到并选择了所谓良性政府治理的道路。舍此,恐怕任何的单一因素都难以对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如此成功进行圆满和清晰的解释。
问题二:中国良性政府治理的历史、文化和环境根源在哪?
历朝历代通过长期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很好地解决了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处理了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用现代的语言可以称之为“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用一个更具概括意义的词语可称之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
上面的这个说法,恐怕会马上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因为国内、外的很多经济学家可能并不熟悉中国的历史,也不大清楚过去两千年中国历朝历代政府在协调历史、文化与环境问题上所进行的长期探索,积累的成功的经验以及经受的那些失败的教训。
因此,他们提出的对中国过去三十年成功经验的总结便大多来自西方的经济理论模型或者现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模型或理论都是所谓的短期均衡模型,而且也往往不能很好地考虑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因素并模型化它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因而往往难以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功进行圆满和深度的解读,也不能很好地提出应对目前面临的挑战的对策并找到中国经济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道路以及政府如何良性治理的制度框架。
首先从中国适宜农业耕作的气候、地理条件谈起。中国从南到北,共跨越热带、亚热带、温带、亚寒带、寒带五个气候类型;同时,中国拥有非常好的季节性季风条件。每年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季风刮遍中国大地,这时候恰好是中国的冬季,往往能给北方地区带来降温和降雪。相反,到了每年春、夏季节,来自太平洋、印度洋的湿热季风便会从西南、东南向北运动,丰富的降雨往往能够覆盖中国50%左右的国土,这恰好给从南到北的植物生长带来了理想的降雨条件。
从地理条件来看,中国西高东低,夏季季风来临时,随着地势的提高,就必然导致降雨活动的发生。我国两条大河——长江、黄河自西向东延伸到大海,这两条大河及其支流相关的流域占据了中国国土45%的面积,从隋唐时期就已经成为中国最具有利条件的农业生产耕作区。
在这些有利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中国的农业自西周繁荣起来以后,就成为历朝历代经济体中最主要的生产活动。在如此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历朝历代的政府很难不重视农业生产,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商人相对于农民而言的极大流动性以及唯利是图本质,因此,自秦汉以后,中国就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对于农民而言,安稳务农、勤奋耕作是本分,刻苦学习是积极向上的表现。
在这种自然和地理条件下诞生的儒家思想,很难不尊重这些天时地利。“君臣、父子、夫妻、老幼”这种相互尊重、和谐和睦的社会关系自然会受到重视。尽管中国春秋早期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四大家,但只有儒家的思想很好地契合了当时政府要求安稳、和谐统治的愿望。
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成为政府认可的“国家宗教”。它虽不是类似于基督教、佛教的真正宗教,因为它不是能够统御人们思想和精神的超验力量,但它胜似宗教,因为它能够占据思想者、知识分子和农民商人的心田,成为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并且它的确有利于农耕社会的稳定、和谐与繁荣。结果,接受它教育的农家子弟拥有了上升的通道,即使那些富裕之后的商家子弟,也必须经受儒家思想的“洗礼”,这样他们才能拥有正统的社会地位。对统治者而言,让大家安心务农,重视社会和谐,扶持尊老爱幼、夫妻恩爱、君臣相安的社会秩序,这难道不是最优的社会选择吗?
按照理论,经济发展演进中一定存在着无数种可能。但在中国优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我们发现,经过无数次的自然试验,一种经济、文化和制度均衡最终胜出。就让我们顺着历史发展演进的轨迹看看,中国良性政府治理之所以最终产生的原因吧。
在西周时期,中国主要的统治形式是所谓的封建制。国家主要由一个王室统治,然后国王将全国的不同地区分封给不同的王侯去统治,这些王侯各自拥有独立的财政、军事力量,只有在外敌入侵的时候,诸侯才有义务响应国王的号召一起起来保家卫国,战争结束大家各自回家,经营各自经济和生产事务。后来这样的统治方式随着不同诸侯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变化而逐步瓦解。到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开始相互讨伐,扩张各自版图,最终秦国因为很好的发展战略,治理经济、军事的得道有方而统一全国。
自秦以后,中国成为大一统的国家。皇帝通过郡县体制管理全国,国家拥有专业的军队保家卫国,农民专心务农,商人的利益逐步被边缘化。当时,任何人无论贫富贵贱只要勤学苦练《四书》、《五经》,一心向上,都可拥有进入官府的通道。两汉时期,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开始正式成为“国家宗教”,并经过很好的实践。此后,三国、两晋时期、南北朝时期,中国气候变冷,北方游牧民族南迁,开始影响中国大地,中国曾经出现过所谓的“坞堡统治”,不同的小国占据一定的有利地势,相互之间常年征战。隋朝时期,中国正式以科举考试的形式选拔官员,帮助国家统治和管理硕大的疆土。
隋唐以后,气候转暖,中国再次恢复大一统统治,政府治理再次采取“中央集权的政府治理模式”。两宋时期,中国开始遭受越来越多游牧民族的南迁,原因同样是自宋朝开始中国的气候开始渐进转冷。游牧民族以及汉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人口大批南迁,来到了南方水草更丰美,人口更加密集的江南地区,这样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提升,商业氛围加重。但是两宋政府不了解这些,整个统治模式仍然采取“中央集权的政府治理模式”。为防止将军谋反,实行兵将分离以及所谓募兵体制,结果因国家不能组织有力的抵抗,最终宋朝被少数民族所灭。由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一开始试图推翻汉族建立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实行畜牧经济,结果最终还是出现内部纷争,国家灭亡。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再次走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体制”。此时此刻,虽然气候变冷的客观条件到后期逐步好转,但是由于西方科学技术、军事技术在15世纪以后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宗教领域的改革、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以及此后的工业革命与政治大转型,结果于1820年后全面超越中国,并开始以军事和武力寻求广阔的工业品市场,最终明、清覆亡。
清朝灭亡后,中国再次面临着分权和立宪政治体制。国民党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本应该是现代的立宪体制,但接下来长达十多年的军阀混战,最终是蒋介石一党专制。在经济治理上,蒋介石政府成立之初,主要依赖西方财团,其人才和智力资本也大多来自在美国和日本受过训练的西方正统。因此蒋介石时期建立的政府也主要是大资产阶级、银行家联合专政的政府。占人口70%的农民,占国土面积80-90%的农村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蒋介石政府建立的民主立宪体制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军国独裁主义的翻版,而以土地改革、惠顾农民为导向的中国共产党便迅速壮大,并在28年内占领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面临着创新政府管理体制的机会。依赖于历史上的中央集权治理模式好像非常不现实,恐怕也会被人带上“封建经济”的帽子,学习国外条件也不成熟。最后,只好全面照搬了对中国长期友好的苏联老大哥的“全面计划经济模式”。到后来,出现了所谓的“三反”、“五反”、“大跃进”,不顾中国经济基础和比较优势原则,大炼钢铁,试图短期内赶超英美发达国家;在国家体制上,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各种运动占据思想阵地,儒家思想荡然无存,小农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这样,自然灾害的冲击加上人为治理的失误使中国经济走向了破产的边缘。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既是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大修正,而且更是一种政府治理模式的大调整。小农经济受到尊重,乡镇企业得以出现。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受到尊重,一直存在的“亦农亦工”的小商业得以复活,中国历史上很好的地理气候、环境因素再次得到很好的匹配与协调,同时中国迅速打开国门,迎接外商,中国由于技术落后的“后发优势”得以发挥。加入WTO之后,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因有了世界市场的支持而得到迅速发挥。
如果我们从中国过去长达两千年的政府治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看,中国自秦朝起2232年的历史,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模式占据了81%的时间,而所谓的封建分封体制、列国体制、坞堡体制、军国体制占据了19%的时间。
自西周开始,人口从2000万增加到14亿,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的成功,为什么?因为历朝历代通过长期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很好地解决了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很好地处理了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用现代的语言可以称之为“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用一个更具概括意义的词语可称之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管理体制在演进,最终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体制胜出。诸多的学说和思想相互竞争,最后儒家思想胜出。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中国人胜出,曾经在中古的很长时期内领先于西方,只是在近代落后于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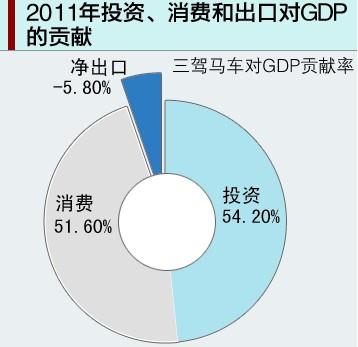

问题三:未来二三十年的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
中国完全拥有继续增长二十、三十年的有利条件:广阔的国内市场需求;80-90%的城市没有地铁系统;家庭车辆拥有比率低;人均GDP比发达国家低。
说到未来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很多的经济学家大多会语焉不详,或者会根据现有的西方短期经济理论进行简单预测。按照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国还要继续对外开放吗?如果中国经济已经全部对外开放,开放程度为100%,我们还需要对外开放吗?
同样“财政分权说”也不怎么靠谱。在历史上,我们绝大多数时期采取了中央集权式财政体制,结果中华民族生存繁衍了数千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只在1994年之后实行了较好的财政分权,结果这就成了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难道未来三十年的中国还要一直实行财政分权吗?从中国历史上来看,财政分权还是集权只是政府管理经济体制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形式,到底采用哪一种体制完全取决于国家的实际需要。
唐朝后期曾经实行了很好的财政甚至政治分权体制,结果政府的统治由于受到藩镇割据的影响,导致了唐朝自755年之后长达100多年的衰退。相反,中央集权体制是否一定好,也完全取决于国家和经济的实际需要。宋朝面临着很大的外部挑战,主要是西夏和金从西、北方向入侵的压力。按照道理宋朝最好要实行财政集权,结果政府的确实行财政集权了,从农业收税,让商人开门经商,也从商业收税,但钱却没有用到正当的军事用途上。相反,在军事管理上,宋朝应该实行一定程度的分权,可是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发家史使他担心分权导致政权的丢失,结果却太过集权了,这样,打仗、练兵时兵、将相互分离,结果对外军事上连连失利,导致国家覆亡应该在所难免。
未来中国经济能否还能继续增长二十、三十年?如果根据资源、文化、环境等条件来看,我们完全拥有继续增长二十、三十年的有利条件。
第一,中国存在着广阔的国内市场需求。
中国目前还有49%的人居住在农村,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1%,这与发达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其实,这个城市化的计算依据是以人口在城市居住一年以上为基础计算的,这其中还有很大的误差,因为很多农民工在城市居住时间超过一年,但他们的家庭、户籍、房子都还不在城市,如果将这部分人从城市化当中减掉,中国的城市化率可能还没有这么高的比率。如果现在让那些还未完全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以及其余的人都拥有城市户籍的话,由此带来的住房、建筑、生活消费数额将无比巨大,将至少能够保证中国经济再飞速增长20-30年。
第二,现在中国80-90%的城市都没有地铁系统。
如果按照北美人口50万的城市就铺设地铁来计算,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要为几百个够条件的城市铺设地铁,这项投资产生的需求将是非常惊人的。想想看,再加上由于地铁修建相关的钢材、道路、公交、车站等配套设置,这将产生多大的市场需求。
第三,中国目前家庭车辆拥有比率约为4.6%,尽管近年来车辆拥有率快速上涨,但是仍然不会超过7%。这与目前全世界车辆拥有率12%,美国75%,欧洲70%的比率差距很大。
如果中国要达到欧美国家车辆的拥有水平,中国市场将至少需求2亿-3亿辆汽车,再加上更新换代的需求几千万辆,由此引发的汽车零件、钢铁、塑料、电子、橡胶需求也将是非常巨大的。
第四,中国2011年的人均GDP只有5444美元,欧盟34847美元,美国48441美元,中国的数字只有欧盟的七分之一,美国的九到十分之一。
如果中国的人均GDP增长到美国2011年的水平,中国将至少需要二十到三十年的时间。
问题四:未来如何处理好四个重大问题与关系
中国文化怎样实现从纯粹儒家思想到恰当地融合契约思想、从和谐转变为承认一定的个人利益冲突、从依赖关系到依赖法治与制度建设。
上述说法只表明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拥有继续高速增长的可能,但是否成为现实,还需要很好地解决影响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以下若干重大问题与关系:
第一,中国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如果不说是全面恶化的话,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比改革开放前恶化了。
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目前60-70%的土地受到化肥、各种化学物质的污染;中国60-70%的河流受到工业污染。如果说这样的数据不完全反映官方的报道,那么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我们也发现情况的严峻之处。
2010和2011年中国面临灭绝威胁的鸟类品种分别为85和86种,受威胁的鱼类品种为97和113种,受威胁的哺乳动物品种为74和75种,受威胁的植物品种为453和374种;而美国面临威胁的鸟类品种为74和76种,受威胁的鱼类品种为117和83种,受威胁的哺乳动物品种为37种,受威胁的植物品种为245和219种。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以及环境方面的很多指标比美国要更加严峻。
另外如果以每2000美元GDP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2007年和2008年,中国的数据分别为美国数据的5.77倍和5.55倍。按照遭受旱灾、水灾和极端温度人口所占的比率来看,2009年中国的数据为7.95%,而美国只有0.21%,中国的数据为美国的38倍。今后我们到底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二,从中国文化来看,儒家思想向来强调人们之间关系的尊卑长幼,上下级的级别和社会关系序列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这种文化是产生于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合宜性和正当性。但是文化一旦形成,要发生变迁就非常慢,大大慢于经济基础的发展速度。
现在我们的经济基础已不是小农经济,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达到了非常低的水平,现在的经济基础已经完全是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基础上的高流动性、非人际化社会关系网络,其结果是,儒家倡导的邻里和谐、上下级和谐几乎全被利益、个人自利所取代。这样,契约关系、诚信体系、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就比以往显得更加的重要。同时人际关系、邻里和谐、上下等级都趋于弱化,非人际化关系将逐步占据主流。
所以从文化层面看,中国文化怎样实现从纯粹儒家思想到恰当地融合契约思想、从和谐转变为承认一定的个人利益冲突、从依赖关系到依赖法治与制度建设,这恐怕又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从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经验来看,我们发展了经济,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化建设。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说明了我们如何找到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体制的极端重要性。
第三,从政府治理来看,我们也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治理模式是有利的自然地理与小农经济基础上诞生的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管理成本最低,对农业经济管理最为有效,被中国历史上81%的朝代所选择。
但是今天中国面临的小农经济基础已完全不同于以往,我们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出口贸易大国。这种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时代所需要的政府治理肯定不同于以往,中央集权的政府治理是否还可行?是否仍然非常有效?现在已经存在很大的疑问。
过去农民不怎么流动,在此基础上所采取的一系列集权的措施都行得通,但是商业经济、工业化、国际化时代经济体面临的信息千变万化,如果仍然实行中央集权政府治理,肯定将出现政府治理与现实经济情况的脱节与滞后。如果脱节与滞后就不能及时地协调经济、社会关系,就难以很好地对外部环境变化作出应对,这样经济体出现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第四,过去农业经济时代的社会关系存在着比较稳定的身份序列,社会平等的观念还远未深入人心,家长制、长官意志普遍盛行,这主要是缘于社会流动性低、人口迁移少。
到了全球化时代人口迁移将成为常态,信息万变将成为日常生活,经济体由于交易关系的扩大,交易双方无论年龄、身份、性别将变成平等的个体,这样原先的身份序列将被很快打乱,人们对平等、诚信、相互尊重的要求会增加,人们在经济上对平等机会、平等参与的要求必将上升,这些恐怕都要通过政治制度、政治权利的形式得以确认。
这就必然导致将来的政府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向西方的民主治理模式靠拢。这些我们是否准备好,到底靠拢还是不靠拢,怎么靠拢?等等,恐怕都是我们将来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但是需要协调好很多重大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协调必然依赖于政府治理制度、治理模式的调适和变化。
虽然我们难以一下子看出这种政府治理模式的大致面貌,但是却能看出它一定需要所谓的良性政府治理,也就是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之间是否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相互脱节、相互冲突与互相矛盾,这样,中国经济再出现另外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良性政府治理怎样发挥作用?
评论
编辑推荐
18 vi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