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为何偷换“决策力”概念?
—— 再评“环球社评”《编织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决策是一门科学,科学与权力无关;决策力是一种能力,也与权力无关。“决策权”与“决策力”不存在必然因果联系。《环球》偷换“决策力”概念为“决策权”,进而导出“限制权力”与“决策力需求”二律悖反,这是非常荒谬的无稽之谈,其用意何在?
《环球时报》在习总书记发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重要讲话后,立即发社评《编织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使人感到似乎习总书记疏漏了这一要义而由《环球》来补充提醒。通览全篇,可见其对“权力入笼”忧心忡忡,生怕中国方向搞偏——编出个“同西方一模一样的制度笼子”。笔者已对《环球》此篇缺乏逻辑而不靠谱的社评予以比较全面的剖析与评论,在此不赘。因为依中国《宪法》和法律编织限制权力的“制度笼子”肯定是“紧扣中国实际”的,怎么着也与“西方”八竿子扯不上——即如一头中国母牛不可能生出“西方”小马仔一样。
这里,笔者倒想与《环球》专门聊聊“决策力”问题,因为《环球》将“决策力的需求”与“限制权力”视为“二律悖反”的矛盾命题。
一、揭开《环球》偷换“决策力”概念的魔术黑罩
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几乎时刻面临着各种“决策”,都需要有“决策力”,否则一事无成。对于政府领导来说,“决策力”自然更重要,不论国家大小。
为了让习总书记以及高层领导“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要悠着点、“清醒”点儿,《环球》苦口婆心地提醒:“限制权力”与“决策力需求”是“二律悖反”的——请看《环球》原话:“中国国家大,底子薄,发展的任务相当繁重,这要求政府扮演比在西方国家更积极的角色,对决策力也有了更多现实需求。中国限制权力的真正难点在于如何化解它与上述需求的二律背(悖)反”(亦即相互抵触)。
当《环球》把“限制权力”与“决策力需求”联系起来并判断它们是“二律悖反”的两个命题时,这其实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环球》看来,权力大小和受限状况与“决策力”强弱是成正比的,换言之,“决策力”=“决策权”。《环球》的逻辑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偷换概念吗?甚至难避故意鱼目混珠之嫌。
《环球》对“决策力”虽未作明确定义,但依其所言的逻辑并不难准确推出其偷换概念的事实。不过《环球》将“决策力”与“决策权”混为一谈,在它前一天的另一篇社评中得到侧面佐证:那就是奥巴马“改不动”,而中国改革举措连连,成效显著。——是啊,奥巴马的改革法案、救市举措出台确乎磕磕绊绊,因为国会权力与总统权力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国会不通过,奥巴马的法案便不能生效,国会通过的,奥巴马不签字也不能实施——在《环球》眼里,美国总统“决策力(权)”可谓“弱”矣,“改不动”啊!——这从侧面佐证《环球》是一直悄悄或在潜意识中把“决策力”概念偷换为“决策权”的。因为《环球》所说的奥巴马“改不动”其原因固然很多,但直接原因确是因总统决策权力依法受到约束。
概念正确是判断的首要条件,概念一旦被偷换,何谈正确判断?“决策力”难道主要是指拥有怎样的“决策权”吗?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许多问题和弊端正恰恰缘于如《环球》这样有意无意地偷换了“决策力”概念造成的,它甚至错误地被肯定为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决策力”≠“决策权”,二者也无必然联系
决策是一门科学,科学与权力无关;决策力是一种能力,客观存在的能力自然也与权力无关。权力大者并不等于决策能力一定就与之成正比,正如我们没有根据说我们邻国那位年轻的80后至高掌权者一定就是该国政治智慧和决策能力最优秀者一样。
那么,究竟什么是“决策力”?
在管理学上,“决策力”是指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在掌握大量有关信息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备选方案,从中选出最佳方案(亦即正确决策)的智慧和能力。决策时总是议而不决固然不行,但决策的正确与否更重要——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正是对于正确决策重要性的形象表述。
由此可见,不论个人还是集体、大国还是小国,都非常需要“决策力”(决策的智慧与能力)。管理学还告诉我们:要做出正确决策,必须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必须正确运用“三圈理论”(三圈:决策能否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或机构有无能力实施、执行者的理解和支持度如何等等),必须遵守决策的法制程序。
对于政府来说,不论大小,在非战争或特殊状态下,对决策正确的要求必然远远高于决策的过程时间。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必须认真权衡,广泛搜集信息,听取各方意见,遵循必要的法定决策程序,以确保决策正确科学,把失误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决策的正确性、果断性、过程的程序原则缺一不可,“决策力”的完整内涵难道不基本是这样吗?这是管理学常识。
值得注意的是,《环球》不仅悄悄把“决策力”概念偷换为“决策权”,而且避开习总书记所言“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语境和前提——即依中国《宪法》与法律构建权力之笼,而不是任意限权,更不可能会“编出同西方一模一样的制度笼子”。《环球》作为党报,有意无意脱离语境和前提任意曲解习总书记讲话,偷换概念,进而荒谬地推出“限制权力”与“决策力需要”是“二律悖反”的谬论,误导公众和领导,这是要不得的。
鉴于如上分析,我们在下文若看到《环球》所言“决策力”是应将之视为“决策权”的代称才是符合《环球》自身逻辑的。
三、如《环球》所言之“决策力”给一些国家曾带来长期、深重的灾难
《环球》所说那种强有力的所谓“决策力”,在中国历史上造成的灾难大大多于成就。
中国封建王朝数千年,皇帝及老佛爷的权力几乎无限制,如《环球》所言“决策力”倒是很强的,任何事项,皇上一拍脑袋即可一锤定音成为不可违逆的决策——圣旨,决不可出现如奥巴马那样的“改不动”。可结果如何呢?华夏中国从万国来朝的泱泱中央帝国衰落为被列强小国瓜分欺凌的弱国,背负多多国耻,无须一一道来,究其原因难道不归结于出自皇宫里各种一锤定音的错误“决策”?
1949年以后,中国党政一锤定音的“决策力”同样强大,集中力量确实办了一些大事,政府几乎包揽统领一切,一个号召、一个文件,全国全民必须响应,决策的权威性果断性那确是奥巴马和中国现任领导都无法比肩而望尘莫及的!文革后期有位外国领导访问中国时,面对中国政府一声令下百姓非常听话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曾感慨万端:在中国当官真好啊!呵呵,其意味可谓深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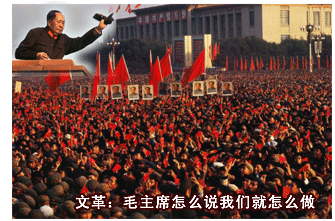 固然,在如此“决策力(权)”下也有过一些正确的举措,但起码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错误决策过多,导致国家综合国力发展缓慢,百姓生活改善甚微,一些地方甚至倒退,几十万大陆民众纷纷冒死偷渡逃往“资本主义”香港延续二十多年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就是最好佐证之一。
固然,在如此“决策力(权)”下也有过一些正确的举措,但起码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错误决策过多,导致国家综合国力发展缓慢,百姓生活改善甚微,一些地方甚至倒退,几十万大陆民众纷纷冒死偷渡逃往“资本主义”香港延续二十多年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就是最好佐证之一。
而随着毛泽东被捧上个人崇拜神坛后,所谓“决策力(权)”就更强了——但如此不受制约的“决策力”带来的却是直接导致“大跃进”的严重错误,接着便有数千万百姓饿死的更严重后果;工业上不得不全面调整以度过经济崩溃的危机,一千多万工人被迫“下岗”回家或去农村(那时称为“精简”职工)。这样具有权威而不受制约的“决策力”发展到文革就更加登峰造极了,所谓“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是当时报纸上几乎天天可见的;毛的团队中任何人已经无法对其决策提出任何不同意见,倘有人敢为,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等等等等下场已摆在那里“示众”!而十年浩劫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也无须笔者细说了。
中国上世纪“大跃进”等相关决策失误和已被彻底否定的“文革”错误决策带来十年浩劫的恶果,都无可辩驳地地证明:“决策力”(正确决策的能力)绝不等于“决策权”。
纵观历史,归纳起来,奇怪的现象起码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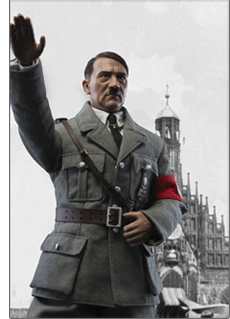 其一,如《环球》所言那样一锤定音的强“决策力(权)”稍稍被制约一点,决策民主稍稍多了一点,中国却反而令世界瞩目地迅速崛起了!岂不怪哉?
其一,如《环球》所言那样一锤定音的强“决策力(权)”稍稍被制约一点,决策民主稍稍多了一点,中国却反而令世界瞩目地迅速崛起了!岂不怪哉?
其二,“决策力(权)”更“弱”、建国史短到只有中国的零头、被《环球》嘲笑“改不动”的美国,其综合国力及科技军事诸方面却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如此“改不动”的奥巴马却又获得连任,岂不怪哉?
其三,德国纳粹首领希特勒统帅部,就《环球》所言那种“决策力(权)”不可谓不强,且国内支持者也甚众,然给本国和人类带来的灾难恰恰也最深重,岂不怪哉?
于是,我们是否可以换个角度再想一想,如果毛泽东乃至希特勒的“决策力(权)”稍稍受点制约,中国乃至二战中的德国以及世界是不是会少些灾难而发展更快?
四、“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科学性、合理性无法撼动
依法治程序制约的“决策力(权)”和没有制约或很少制约的“决策力(权)”相比,前者在决策的时间效力和权威性上自然不如后者,《环球》所嘲笑的奥巴马“改不动”即是一例。但前者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决策失误,这是无疑的。很无奈,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政治决策制度发明出来,基于历史的诸多教训,我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俞可平教授也承认民主有《环球》经常诟病的诸多缺陷,如奥巴马改革方案出台磕磕绊绊、还有游行抗议等等;但俞教授明白而不含糊地如是说:“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或者说是最不坏的制度”。笔者认为这是尊重实践检验标准和历史经验的实事求是之论。
一句话,“权力”或曰“决策权”是个好东西,没有它办不成大事;但“权力”如不依法限制,它一定不是个好东西,能干的事儿十有七八可能是坏事——国家越大,危害的广度和深度也就越大。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我们岂能让所谓超强“决策力(权)”导致的“大跃进”一类波及全国的人为灾难重演?
所以,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其中包含着规范授权和依法限权两方面的因素,并非脱离语境和前提的一味限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一依中国《宪法》提出的观点和部署,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已为历史和现实所论证,无法撼动;也无须《环球》自作聪明加上什么“紧扣中国实际”限制语,依中国《宪法》和法律编织的“制度笼子”也绝不可能是“西方”的。
五、结 论
哲学层面的“二律悖反”现象的确也有存在,但《环球》用偷换概念伎俩捏造的二律悖反论,恰恰是无法成立的无稽之谈,应放入电脑“回收站”——因为“决策权”和“决策力”的鱼目混珠,是很容易将某些领导和公众引入认知和实践歧途的。笔者欢迎《环球》以理论、事实和严密的逻辑反驳本文。
《环球》作为党媒,岂能以骗人的谬论误导公众和高层领导,钝化实施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决心?奉劝《环球》好好读读管理学教科书和有关“决策力”和专断滥用“决策权”的专题历史,认真揣摩科学发展观,再不要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乱发谬论误国误民。□
2013年1月26日
【参考文献资料】
1、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2013年1月22日)
2、《环球时报》社评:编织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2013.1.23.)
3、《环球时报》社评:看奥巴马改不动,而知中国有多难(2013.1.22.)
4、应学俊:评《环球》“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
5、【视频资料】黑潮——逃港三十年风波纪事
6、【视频资料】“决策力”案例:冒进与反冒进 /“大跃进”的决策/
文本:南宁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