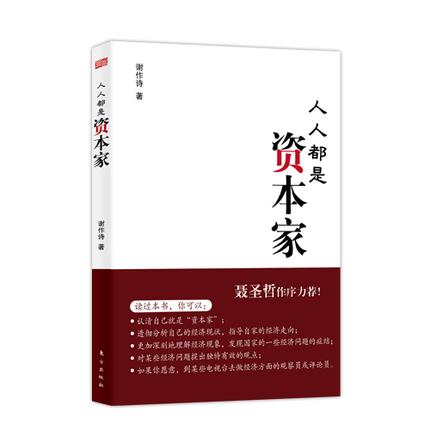柴静的《雾霾调查:穹顶之下同呼吸共命运》,当天点击过亿,好评如潮,但也有吐槽的声音。
有不同声音,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好事。我不否认,调查片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例如确实有煽情的成分,又如对雾霾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等事实与数据的把握,可能有些简单化,再如多少传递了一种缺乏管制的市场导致雾霾这样的理念。但我认为,瑕不掩瑜,这些都丝毫不能抹杀柴静的辛勤劳动与伟大贡献。
还有人批评柴静只是展示了雾霾的现状,却没有给我们分析导致雾霾的深层原因。但是她让我们了解了雾霾事件的种种细节,这就够了。柴静的贡献不在于给予我们答案,而在于引起我们思考。我就借这股东风,谈一谈环保以及与之相关的话题。
只有市场缺失,没有市场失灵
滥施化肥,这被认为是破坏环境;滥伐树木,也被认为是破坏环境;滥排污水、烟尘,都被认为是破坏环境。可是,由于凡事都有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完全不施肥,不砍伐,不排放,虽然对环境没有破坏,但是人类也会因此而无法生存。人都不存在了,再好的环境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见,绝对不是一切施肥、砍伐、排放都是对环境的破坏。这就引出如下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滥”?施多少肥、砍多少树、排多少污才合理?为什么人们要滥施化肥,滥伐树木,滥排污水、烟雾呢?
假如土地是你的私有财产,那么你不会过度施肥,以致损害了土地的肥力。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粮食增量的边际价值不能超过对于土地肥力的边际损害。假如山坡是你的私有财产,你不会过度砍伐,以致山坡的价值受到损害。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木材增量的边际价值不能超过对于山坡生产力的边际损害。在使用资源的过程中,只要使用资源所带来的价值,大于对资源所造成的价值损耗,那么就不是滥用。反过来,因为化肥使用不足、砍伐树木不足,排污过度受到限制,而减少了资源的总价值,这其实也是滥用,是另一种滥用。
经济学的标准虽然科学,但是不容易观察,更不好度量。好观察、易度量的指标是什么呢?
农民在自留地里多用农家肥,而在包产田里多用化肥;在自留坡上栽树,却在集体的坡上砍树。这个朴素的事实让我们找到了度量“滥”的好观察、易度量的标准,同时,也能让我们理解造成“滥”的根源。
农民在包产地里所施的超过自留地的化肥量,就是滥施的化肥,在集体坡上砍伐的超过自留坡的木材量,就是滥伐的树木。而造成滥施化肥、滥砍树木的原因,则在于产权没有被界定为私有。
环保历来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例子,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谓环保的困难,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因为市场缺失。市场有前提,即产权要清晰界定给个人。不能把产权没有清晰界定给个人的问题归结为市场失灵。滥施化肥、滥砍树木等等所谓的环保问题,其实是没有把产权清晰界定给个人的问题。
但是界定产权是有成本的,在有些情况下成本还高不可及,因而无法把产权清晰界定给个人。比如排放烟尘和污水,我们没有办法在空中做一面高墙,以阻止烟尘飘向他人的领地;我们也没有办法在河里建设堤坝,以阻止污水流向下游。这种情况下,环保的问题就真的来了。但这也不是市场失灵,同样是没有市场发挥作用的问题。
在没有市场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排放多少才是合理的,才不是滥排滥放呢?
不同的人来做决定,答案显然不一样。喜欢户外活动的人可能宁愿少一点GDP,也要清洁一些的空气,而宅男宅女可能正好相反,他们愿意牺牲一定程度的空气质量,以换取多一点的收入;河岸边的人会选择要清澈的河水,但是远离河流的人可能会选择GDP。那么谁来决定排放的数量?
同样的人,选择不一样的决策机制,答案也会不同。一种办法是全体人民投票决定,但这个办法费用同样不菲。替代的办法是由全体人民选择政府,由政府来决定排放的数量。放任不管,任由企业和个人随意排放,这也是一种选择。决策机制不同,排放水平显然是不相同的。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决策机制呢?
可惜经济学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经济分析既不偏重、也不反对改善环境。经济学既不断定哪部分人的意见更重要,也不断定哪种决策机制应该被采纳。但是经济学可以告诉我们,稀缺性和替代选择无处不在;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环境好一些,就要减少一点产出,或者多支付一点费用,反之亦然。当然这种替代并非总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经济学还能告诉我们,只有在市场决策的情况下,才能既反映环境保护的代价,又让每一个人满意,而任何其他决策机制,都不可能完全做到。
没错,市场决策既能反映环境保护的代价,又能让所有人都满意。餐厅是我的,我不吸烟,而你却上瘾难耐,只要你给我称心的补偿,我就会让你吸烟。只要餐厅的空气被界定给明确的物主,那么不管这个物主是吸烟的顾客、不吸烟的顾客、餐厅老板,还是别的什么人,餐厅的空气都能用在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如果物主吸烟,而不吸烟者对空气的评价更高,那么他可以出价把空气的使用权买过来,不让人吸烟。
你不能又说空气重要,又不愿意出最高的价格。这样的诉求是廉价的表达,无法反映真实意愿。或许,你会质疑市场决策对没有钱的穷人不公平。你这样说,问题就没法讨论了。市场给你自由,你可以创造财富,但是不能要求财产平等。经济学还能告诉我们,追求财产平等,那么就不能有自由,人权也不能平等,最终财产权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平等。这样转一圈回来,其实只有市场才对没有钱的穷人是最公平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只要有可能,我们都应该用市场的办法来做决策。这也是市场化改革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而凡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其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无一例外都高的重要原因。
市场虽好,却也昂贵。市场不仅需要产权有清晰的界定(而这需要不菲的成本),而且还要求谈判、签订协议等交易费用不能太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使用非市场决策的原因。
市场可能缺失,但是只要它存在,就一定最有效率、最公平地发挥作用。市场不可能失灵。
环境保护的困难
如果能够用市场来解决,环保问题也要尽可能用市场来解决。这就是我们大力提倡排污权交易的原因。事实上,美国一些地区已经实行购买排污权的措施,比如企业必须付费,才能释放硫化物。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反映污染和环境保护的代价。不至于因为环保而牺牲有价值的经济物品的生产,也不会因为生产不值钱的产品而牺牲环保。一种产品,价值极高,但生产时会产生大量污染,那么厂家可以向生产低价值产品的厂商购买排污指标。而那些生产低价值产品的厂商,就会选择停产或少生产,而把排污指标卖给前者。
并非污染物不是经济物品,人们对它没有需求,所以没有市场交易。如果产权能够界定给私人,我的污染物只能排放在自己的空间里,但是生产的产品价值足够高,那么我就会向他人购买空间以排放污染物。
核心问题还是在于产权不能完全界定给私人。而且排污交易涉及面大,交易费用可能太高。因此环保问题或多或少要涉及到非市场决策。即使是排污权交易的情况,排污的数量还会是一个非市场决策的问题。
能够用市场解决的,都不是公共问题。而无法完全用市场解决的,多少都带有公共决策的性质。
产权不能界定为私有,资源就会被过度使用。公园树上的苹果,还没有熟透就被人摘光;公共海滩上,到处是弃置的垃圾;大海成了废物的超级垃圾场,天空成了烟尘的自由排放区。人类要生存,于是就不能不利用公共决策机制对污染排放做某种限制与约束。
但是没有了市场来发挥作用,该如何确定污染的代价呢?
可不可以借助科学来计算污染的代价呢?
以雾霾为例。按照Turner等人的研究,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的PM2.5浓度,会导致肺癌死亡率上升15%-27%。按照这个算法,光是大气污染一项,就能导致中国的肺癌死亡率比欧美高出300%以上。但在实际情况中,中国的肺癌死亡率虽然略高,却远未达到如此夸张的程度。这说明,雾霾与肺癌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容易计算。
雾霾的危害具体有多大?这在科学界其实并没有确切的定论,事实上也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完全没有雾霾,肺癌可能下降,但是收入也会因此而下降,人们会没有能力发现并治疗别的病,疾病率反而可能上升。
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就PM2.5的浓度而言,云南是全国环境第二好的地方,而北京则是倒数第二。然而,北京和云南的人均寿命却恰好倒了个个:北京全国第二长寿,平均寿命80.18岁,云南则倒数第二,平均寿命只有69.54。这就是经济发展、医疗资源的增长带来的好处,它抵消了环境带来的危害。
经济水平对于健康的影响要远远超出雾霾的污染值。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哪怕再环保,其平均寿命也要比污染大省低。在中国,东部省份平均每个人能比西部多活十几岁。事实上,如果做回归分析的话,各省的PM2.5浓度和人均寿命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就是PM2.5越高的地方,人均寿命反而可能越长。这并不是说PM2.5对健康有好处,而是说在污染高的地方,往往经济也比较发达,它对你健康的补偿要大于污染带来的损害。因为你有条件定期体检身体,及时治疗疾病,并能接受更好的医疗服务。
而更复杂的在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替代关系。计划经济的时候,生活水平比现在低很多,然而我们不得不闻刺鼻的煤烟,因为只能低效率地散烧煤炭。工业化、城市化不仅提高效率,而且还因为规模经济,可以集约化治理环境。再者,成本收益的计算要考虑到各地、各人,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这个地方生产钢铁水泥产生污染了,别的地方土路变水泥路,扬尘大幅减少了;城市的污染增加了,然而农村山青水绿了。这些代价与收益,科学是算不出来的,否则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
然而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计算雾霾的代价很困难。就算科学能够清楚地计算出雾霾的代价,问题是人们的主观评价也可能大相径庭。我的老家青山绿水,父辈们就没有八十岁以下的,然而我宁愿选择到雾霾严重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也有人仅仅是为了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就放弃较好的工作,选择移民国外。
公共决策的存在是因为产权不能完全界定为私有和存在外部性。多数时候不得不赋予政府或某个委员会权力,委托其做决策。然而权力同样存在外部性,甚至可能是更严重、更加不容易纠正的外部性。没有理想的决策机制。环保问题比较可行的办法可能是大多数人满意原则。这并不是说大多数人满意就是好,而是这个原则是比较可行的选择。当然实际的决策机制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
但即使是全民投票,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因为投票行为同样存在外部性。
这就是公共决策的困难:公共决策的结果既不能完全反映代价,也不能让所有各方一致满意。公共决策只能是用一种有外部性的行为去纠正另一种外部性。所以,普通的商务谈判容易达成共识,但是关于环境、大气的谈判就很不容易。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权衡取舍,的确不是容易做出抉择的。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一种环境改善,不但不影响经济发展,反而还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这样的环境改善,没有理由不支持吧?
中国的问题
柴静的贡献,不是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的雾霾多么严重,而是让人们深入思考其背后原因。
不看柴静的调查片,我不知道凌晨的时候污染比白天高峰时还要严重。而原因居然是凌晨向城市运送物资的柴油大卡车没有任何排放设施。这些车一辆的排放就是达标车的500倍,三万辆车进城,相当于几百万辆车夜里不停的在开。交通部门说:车是新买的,还贴了环保部门的环保标。况且物资保障车不允许处罚。车主说:咱也不懂这个,咱只是个买车的,买的是贴了国家合格证的车。车企说:别人造假,我不造假就活不了。如果严格执法,抓那些造假的,我保证第二天就生产真的。环保部门说:大面积造假,或者说全面造假,在这个行业不是秘密。我们口里没有牙齿,连嘴都不好意思张,怕别人看到自己没有牙齿。《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写明只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的缺陷汽车,才召回或者销毁。没有排放设施跟生命财产安全有什么关系?所以没有召回的依据。《大气防治法》规定可以销毁或者强制罚款,但法律制定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被使用过。因为规定必须由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执法,却未写明执法主体。环保部说:听说不是我。工信部说:绝对不是我。质检总局说:应该是我们三个吧。全国人大说:这条法律执法主体确实不明,当初立法的时候,很多部门反对,法律通不过,所有只能这样一个模糊的说法。滑稽不?!
车企还说:我们国四的标准早就已经确定,但是国四的油品迟迟不供,供上来的品质也不高。国内最好的柴油,其排放是美国、欧盟、日本的25倍。汽油标准则长期比发达国家低二到三个等级,而提高一个等级就可以减少10%的排放。那么为什么不把油的质量弄高一些呢?因为国家标准本来就不高啊!企业都是逐利的,没有理由要求企业超越国家标准供给更好的油品吧!为什么不把标准定得高一些呢?原来制定标准的是石化行业的人。而分歧则在钱上,环保部门说国三升国四一升涨7分就够了,石化部门说得5毛。发改委、财政部也抱怨:人家是副部级单位,谁买你的账啊。人家涨价报告上来,涨不涨,不涨就断供了啊。
并不否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替代关系,但是没有任何排放设施,肯定是不妥的吧!
也不否认,简单向发达国家高标准看齐未必就好,但是让石化行业的人自己制定标准也不对吧!
那个中石化前总工程师、石油标准委员会主任,口口声声,标准不能由不懂炼油企业的人来制定。对于为什么不提高油品标准来倒逼油品升级的问题,人家的回答是:升了,因为断供引起社会不稳定,谁来负责?再问:把油品市场彻底放开,这样不就不存在断供的问题了吗?人家答:弄得不好就出大事,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做油品的。可是难道现在的油品比阿猫阿狗做的好?发达国家油品放开怎么就没有出大事?
退一步讲,我们不去与发达国家比油品质量。我们也不再问:纽约、东京人口密度比我们大,人均车辆拥有量比我们高,为什么他们的空气质量比我们好?那么能不能让我们用发达国家的低价格用上我们的低品质油呢?千万不要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还做不到哟。炼油技术是可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满足一价定律,即不考虑运输费用、关税等壁垒,那么同一商品在世界不同地方用同一种货币标价,价格是一样的。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油品质量比发达国家差,价格则比其高,这是否需要反思?
诚然,只是放开准入,让市场竞争,未必就能解决油品的问题。这需要有好的规则,除了有好的环保标准,还要有对执法的有效监督与约束。这绝不是简单的赋予环保部门执法权的问题。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那么赋予政府权力,不但不能解决环保问题,而且还会扼杀经济。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环保部门不作为,或者不能作为,并非是简单的没有牙齿的问题,而恰恰是行政权力过大,得不到监督和约束的问题。环保问题是因为外部性而起,然而世界上最大的、也最难消除的外部性,恰恰是权力问题。
想不到河北是燃煤最厉害的地区,因为河北是钢铁大省。一吨钢铁只赚一个鸡蛋的钱,政府居然还大规模补贴,并且继续将钢铁企业作为支柱行业。调查片说,有个企业政府每两年补贴其20亿元。政府和企业的理由冠冕堂皇:十几万人的就业是大问题;城市化还会继续,只要城市化继续,这些产能就会被消化。
对于第一个理由,我想说的是,你政府不每年补贴这个亏损企业10亿元,就不用每年对别的好企业征收10亿元的税,那个好企业会扩大生产,这不仅能够更好地解决就业,而且还能产生经济效益并减少污染。
而更让人好笑的是,这个钢铁企业拿到了政府的补贴后,竟然是进一步建新厂扩张生产。
中国为什么产能过剩?不是因为政府规划还不够好、管制还不够得力,而是因为产权公有、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官员和国企高管花的是别人的钱,花别人的钱总是多多益善。政府和国有企业不搞投资,钱怎么落到官员和国企高管的口袋中?所以,又要国有企业,又要政府干预,又不要污染,这怎么可能?
另外,中国有没有可能通过深化改革,不影响产生而把电价、气价降下来,让人们少烧散煤呢?
雾霾还可能与老百姓的不当诉求有关系。提高质量或者减少污染会增加成本。如果价格受到管制,那么企业就只能降低品质、偷偷排放,或者关门大吉。所以我们大家也要反思,是不是我们一方面期望高品质和低污染,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出面压低价格了。照理来说,因为垄断,两桶油反而具有通过涨价弥补成本来确保证油品质量的条件。但是成品价格是受到管制的,那么就没有这种可能了。当然我没有说,放开成品油价格管制,油品质量就一定改善。我也必须指出,价格管制未必一定是老百姓的需求,政府有关部门才是最大需求者。
已经不需要去指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并非简单线性替代关系的逻辑了。在1960至1970英国治污的这十年,其经济不但没有倒退,GDP反而增加了一倍。他们用事实证实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可以同步进行。对于中国来说,绝非雾霾多一点经济就一定好一些。事实上,减少一点过剩的产能,雾霾一定会减少一点,而少制造过剩的产能肯定对经济是有利的。所以“还在发展过程中”根本不是环境污染的“挡箭牌”。
简单的总结
环境保护的一般困难,任何国家都要面对,而且确实不容易找到满意的答案。但是中国有其特殊性。
环保首先是产权的问题。如果山林是私有财产,那么你不会把树木砍了去做方便筷,而会像日本人一样保留自己的林地从国外进口。假如土地是私有财产,那么你使用化肥的时候就要掂量掂量,看它会不会伤害土地的长期肥力。如果不是国有企业,就不会有今天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从而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雾霾的程度。
环保也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和我们的不当诉求。如果政府不对那些亏损的能耗企业提供补贴,那么雾霾也会大幅减少。如果政府放弃价格管制,放开准入,允许任何人都可以炼油、卖油,那么在竞争压力下,油品的质量就会大幅提高,雾霾问题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很多情况,不是加强政府管制的问题,而是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然而我们不能不反思,很多管制确实又是我们自己有意无意“求仁得仁”的结果。
环保还在于法治。如果标准和法规制定不被利益集团绑架,并且能够得到严格的执行,那么雾霾也会减轻。
产权私有,打破行政垄断,限制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推行法治,这正是市场化。市场要么正确地发挥作用,要么不存在。只有政府失灵,从来就没有市场失灵。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才是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最有力、最能持续的保障。
由于环境保护存在外部性,市场可能会缺失。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其必要的作用。但现在不是简单的加强管制的问题,而是需要认真思考,权利怎么界定,权力怎么授予,谁来授予,怎样实施管制,又该怎样监督、约束权力。绝对不是无政府主义,但是怎样让政府做好其应该做的事情,的确也不是容易的问题。
欢迎订阅谢作诗的微信公众号:xie-zuoshi
【卖《人人都是“资本家”》签名版,39元,包邮,但需每周集中发一次货:可以通过微店“谢作诗的签名书店”购买(点网址http://url.cn/Zkjf0t或者扫下面二维码);也可以通过银行汇款购买(银行卡号:6227001541200063555,建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户名:谢作诗),还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微信号:zuoshixie)、支付宝支付(支付宝号:[email protected])购买;通过银行汇款、微信或者支付宝支付购买的朋友,请一定写明邮寄地址、收书人姓名及联系电话,如不能在相关留言中标记,请发到18640116699】
非签名版在当当(http://url.cn/aJ2tSO)、京东(http://item.jd.com/11584180.html)、亚马逊(http://url.cn/XsbKjP)、淘宝(http://url.cn/aIPGhc)以及各大书店有卖,有折扣,发货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