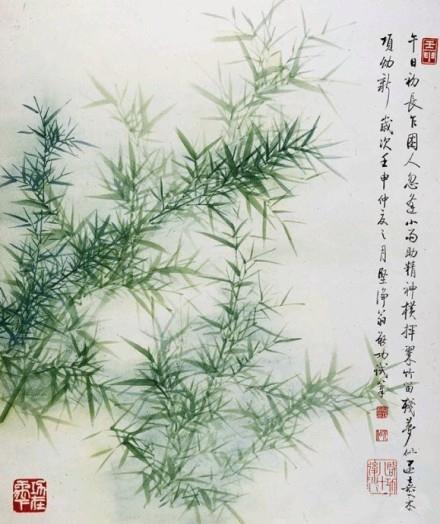
最近,从手机上看到一条流传广泛的微信——《两个惊天大案对社会的影响,发人深省!》这属典型的“标题党”。案子并不惊天动地:一个是中国的,南京街上,一个老人自己摔倒受伤,一个叫彭宇的上去将其扶起,并送到医院,还掏出200元作为帮助。结果摔伤者却把彭告上法庭,称彭将其撞倒,法官判彭赔偿4万元,根据是200元。不是你撞的为什么你要给钱?此事引起社会热议:好人难做。另一个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的案子:一天深夜,一个女子从露台上摔下来成重伤,一个男子路过,乘人之危抢劫了她的钱财,但又不忍心她不治身亡,于是报警后离开。因为那里正好有摄像头,过程被拍下来了,警方将男子抓获。但法官却判男子无罪,理由是:抢劫财物与拯救生命相比,已无足轻重。两个案子不同判法,的确令人深省。
正巧,阅读浦东杂文学会会长吴树德传来的《浦东杂文作品选》书稿,其中就有一篇《两个案例,发人深省啊!》,从文章结构到文字,与上边的微信可以判定为同一篇东西。一篇杂文能在网上流传,说明有相当的影响力。当然,这部杂文选集还有不少“发人深省”的文章。比如《假如鲁迅还活着……》。这个命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人提出过,这些年来不断又有人再提。这无非是想说,假如鲁迅还活着,他还会不会写杂文?写了会不会挨整?坐牢? 结果好像只能猜测,谁也不是终审法官,于是就像祥林嫂一样反反复复地翻腾这句假设。还是浦东杂文作者来得干脆:“与其痴痴不休地假想于‘鲁迅还活着’会怎样怎样……真还不如扪心自问:‘今天我活着’,我们是否也有鲁迅般的勇气和力量去呐喊,去作文,去‘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再弹奏一曲‘广陵散’!”我看这话靠谱,像个杂文汉子!
记得1984年,著名杂文家蓝翎先生曾在我的第二本杂文集《晨曦集》的序言中 说:“鲁迅先生是杂文的开山祖,新起的杂文作者不尊重鲁迅的则尚未听闻,大都一开始就把鲁迅的书当着经典,认真攻读,从中汲取精神的艺术的力量,从而证明了他们是在鲁迅的影响下继承杂文的战斗传统的。鲁迅精神直接影响着杂文作者一代一代的出现,杂文创作对鲁迅精神的继承,比起其他文艺形式似乎更直接更明显,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杂文创作的可贵特点之一。”他还说:“蒋元明同志写杂文的初衷是出于工作需要,因为他调报社后分配在编杂文的工作岗位上。而这个岗位于二十年多前初次确定后,就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鲁迅的传统,提倡新的‘花边文学’,这在当时是起了带头作用的。……我有幸曾在这个岗位上站过第一班岗。”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小人物”蓝翎选调人民日报文艺部,在副刊当杂文编辑,开创了一个杂文新局面。后来他被错划“右派”下放外地。我是1975年大学毕业到报社的,粉碎“四人帮”后副刊恢复杂文,我就成了杂文编辑。蓝翎后来重回报社,先当评论组长,后升为分管副刊的副主任和主持全面工作的主任。对我来说,他是同事、领导,更是杂文前辈、师长级的朋友。我们先后在同一个岗位上站岗,为了同一个目标:继承和发扬鲁迅传统,办好“花边文学”。几十年过去了,我亲眼目睹了一代一代的杂文作者继承鲁迅精神前行。这说明鲁迅精神不死,鲁迅始终还活着!因此,我想说的是,当下的杂文作者,与其扯那些没用的东西,不如认认真真多读点鲁迅,多写几篇杂文,多做点有利于杂文的事情更有意义!
然而,扯没用的东西的人依然存在。几个月前,李庚辰兄转来一篇东西:《当代杂文三十年 ——1984年~2014年》,作者是杂文刊物的一个编辑,主题是“新基调”PK“鲁迅风”,把杂文界划分为两个圈子,一个是“新基调”,主帅刘甲,一个是“鲁迅风”,旗手严秀(曾严修)。还断言,“新基调”只是个新鲜提法,并非新鲜玩意。“‘新基调’……早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从夏衍、唐弢就开始,到今天,展眼各类媒体,众多的“杂文”,骨子里皆为“新基调”。因此,“新中国杂文史基本上以‘新基调杂文’为主流”。——照作者的论调,新中国以来的杂文,主要是反“鲁迅风”的,应当彻底否定。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被封为“鲁迅风”首领的严秀先生刚刚过世,他生前主编过两部杂文大书:《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杂文集》《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我有幸参加了前一部书的编辑工作。这部书一百多万字,花了两年多时间,曾老反复看的送审杂文就有几千篇,费尽心血!他在序言中说: “现在呈献于读者之前的这卷杂文,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的广泛和作者面的广泛,是空前的,这些都大大超过了三十年代和‘文革’前的十七年。” “国家兴,杂文兴;国家乱,杂文亡——解放以来三十五年的杂文史,简单说来,就是这么两句话。”这是严秀对解放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杂文创作的评价。两个广泛,一个空前,再加上超过两个时期,评价何其高!那种“新中国杂文史基本上以‘新基调杂文’为主流”的论调,实际上是在PK所谓“鲁迅风”首领严秀的结论,也是在否定包括严秀主编的两部杂文大著在内的新中国几代杂文作家的成就,这是无知呢,还是有意呢?!
记得在一次编辑讨论会上,有人不同意收入余心言(徐惟诚)的作品,说他左。严秀当场回答:“余心言是写杂文的,为什么不收?”结果,余心言的几篇作品入选了,这就是“作者面的广泛 ”。“鲁迅风”旗手主编,在杂文大系里收了不少后来被圈为“新基调”的作者的作品,使这部百万字杂文集有了“史诗”的地位。有感于严秀老的大家风范,我事后写了一篇《严秀其人也怪》的随笔,其中就提到这件事。严秀老看到了,也写文章回应,说我在“抬举”他。像严秀这样继承鲁迅精神,以杂文事业为重,广泛团结杂文作者,推动杂文创作的风范,值得后来者好好学习。
也有人说,“新基调”、“鲁迅风”的划圈,只是个别人的荒诞行为,没有市场,不用理采。但也有朋友告诉我,说有一位很有头脸的人物主编了一套全国性的杂文系列丛书,就明确表示,凡是“新基调”的人一律不选!我疑心这主儿武侠小说看多了,以盟主的心态竖旗拉队伍。但能否一统江山,名垂青史,那就难说了。
浦东杂文学会是一个成立才两年的年轻学会。前年,在哈尔滨全国杂文学会第27届联谊会上,甘肃省杂文学会的吴树德流露出有意在家乡上海浦东推动成立杂文学会。上海是鲁迅先生最后生活、战斗的地方,我们组委会积极支持和鼓动这件事。结果,浦东杂文学会很快就成立了,去年还成功地承办了全国杂文学会第28届联谊会,并挂牌建立“全国杂文作家创作基地”,又办起了《浦东杂文报》,出版会员作品选,显得生龙活虎,实在是应当给个赞!
当然,更应该给北京杂文学会老会长胡昭衡(李欣)、老顾问高扬等老一辈杂文家点赞,是他们为了团结全国的杂文作家、杂文作者和热心支持杂文事业的人,倡导召开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年会),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求同存异,把鲁迅精神传承下去,推动杂文事业不断发展。这件事一直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因为各地杂文学会都很“穷”,一无经费,二无编制,办会的都是“义工”。到后来,由于主持各地杂文学会的老一辈杂文家年事已高,甚至谢世,“余威”不复存在,联谊会更难办了。在2009年的23届福建莆田年会上,大家商议成立“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组委会”,由各地学会的负责人组成,搭一个平台,负责协商和主办年会。随后的杭州、银川、徐州、哈尔滨、浦东年会都很成功。不少学会都有自己的会刊,淅江杂文学会连续几年承办了“鲁迅杯”杂文征文;新换届的湖北杂文学会今年承办全国“鲁迅杂文奖”评选。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的宗旨,就是以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推动杂文事业向前发展。在鲁迅的旗帜下,学会不分大小,会员不分老少,观点各异,风格多样,百花齐放,与时代同步。
我相信,只要杂文界同仁少一些空谈,多做一些实事,鲁迅就离我们不远。
2015年 8月20日于(北京)怪味斋
(作者:北京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