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对今天的人来说,已经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字眼,而在40多年前,“打工”却被笼上了“搞副业”的面纱。
董志恒是武威城北郊一个名叫“贾家庄”村的农民。1966年五月端午,他和另一位村民偷偷背了80斤韭薹到玉门贩卖,谁知这一去却闯开了一条“打工”路。三年后,董志恒就带领60多个打工的农民,干起了他们的第一个建筑工程。
在40多年前,那个特殊时代,一个农民离乡背井,在外打工,他经历了哪些酸甜苦辣,发生了哪些故事?
10月18日,董志恒讲述了近半个世纪前的“打工”故事。
 |
在玉门市石油公园留影
贩卖韭薹迈出了第一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外出打工纯粹是一个意外。当时,不叫打工,叫搞“副业”,就是以集体的名义外出“打工”,很有些那个时代的特色。
计划经济时代,武威县金羊公社几个生产大队的种植各有特色,分为“粮食作物区”和“经济作物区”。当地老百姓中有句民谣说“马儿坝的西瓜洪祥儿的蒜,海藏寺的挑麻赛扣线”。我家就住在武威北郊的海藏寺附近,属于“经济作物区”。我们小队主要是种植亚麻,村民们都吃的是国家供应粮。但购粮还要付现金,由于我们没有其他经济来源,钱就难住了农民兄弟。国家每月给我们供应30斤粮,细粮只有30%,有些人家先借钱购买细粮,然后将细粮高价卖掉,再反过来购买粗粮,生活十分清苦……另一个方面,我们村人均只有3分地,妇女们就把地种了。这两方面的因素,逼得队长眉头紧锁,男人们只好另寻他法谋生。
1966年农历五月,我们公社种的韭薹到了收获季节。因为我的一个女同学在玉门市百货公司工作,我便向队长请假,和那位女同学的弟弟各背了40斤韭薹,悄悄地出发了……我们此行的目标是玉门油矿,那里的工人多,购买力强。武威老乡也多,遇事也好相互照应。
我们扒上一辆油罐车,在河西走廊的寒风中熬了一夜后,总算到了玉门。下车后一打听,我们背的韭薹不能在街上推销,沿街推销属于违反政策,跑了一天,眼看韭薹蔫了,还没找到下家。
正好走到了玉门市委机关食堂门口,我们大着胆子进去推销。谁知管理员竟是一个1952年就到玉门油矿的武威人,名叫徐云庭,一听口音就对上了头。他二话不说就将我们背的80斤韭薹,以每斤0.80元的价格收了。当时,这个价格就好得不得了。我们队里的每个工分才值0.22元,一斤韭薹相当于四个工分。
这次算是开了眼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每天两元的高工资,我们却落不下分文,不得不想办法
就这样我们就和老徐熟悉了。正好这时老徐管理的食堂要挖排水沟,缺人手,我们两个就毫不犹豫地将这个活揽了下来。挖沟需要的人多,咋办呢?
我们便连夜让一个回武威的老乡带信回去。贾队长一听把带去的韭薹卖了,还联系到了零活,不由分说便大力支持,派了几个愿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从此就算是给乡亲们找到一条“搞副业”的新活路。
那时,外出打工不像现在方便,搞副业的人先在队里开了介绍信,又到大队换了介绍信,再到公社换介绍信。跑上好几天才算把事情办妥。
我们8人从此就正式开始了打工生涯。后来我们又接了安装玉门市委机关食堂下水管线的活。工资给得挺好,一天干八小时两元,这个工资标准是有文件规定的,基本和玉门普通工人的工资相差无几。
按照队里约定,干一天要给队里上交两元,这样我们个人就落不下分文。干了一天,大家的情绪都很悲观。照这样下去,吃饭都会成为问题。这可怎么办呢?最后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加班加点干。挖沟的活是按土方算钱,每方土给0.6元—0.8元,干多自然就拿的多。玉门的电力供应比较充足,晚上也有电灯,给我们帮了大忙。我们天天加班,经常干十六七个小时。这样算下来,干一天能挣5元,除掉给队里交的两元,自己还能落3元。
我们自己做饭吃,午饭和晚饭就提前派人回去做。最难办的是粮食问题,当时一切都要凭票供应,我们吃的粮食都是从武威老家背来的。每隔两个月就要去背一回面粉。那时,我才23岁,年轻人饭量好,便经常把背来的面粉拿到机关食堂里换成苞谷面之类的粗粮。这样就多出几十斤,勉强够我们吃的。
玉门的天气冷,到11月份,室外的工程就不能干了,本来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回家。但大家都没有回家的念头,一来是想多挣点钱,二来是为了节省10多元的路费。这次出来都开了眼界,不仅见到了许多在农村没有见过的东西,而且还看了电视机里的另外一个神奇的世界……
我们跟着玉门油矿的工人师傅干室内装修之类的活计。8个人都分开了,有人跟着电焊工,有人跟着电工,唯独没有人跟木工,因为我们老家的木工力量很强,有好几家是祖传五六代的木工师傅。
一来二去,我们都学到了不少技术。尤其是电工技术。在老家都点的煤油灯,对电还是非常陌生的。渐渐的我们对电也熟悉了。1967年春天没有回武威,直到1968年的春节前三天我们才回到老家。
尽管大家赚了点钱,但都没有拿到手里。那时,一切经济往来都采用“公对公”的方式,我们赚的工钱,都被玉门建设单位汇到了生产队的账上,队里到年底再给我们换算成工分。我们向玉门建设单位借的“伙食费”,也要等到来年偿还……所以只能依旧扒火车,从武威到玉门这条线跑得多了,我们也掌握了火车的发车规律,一般每天都要往武威发送一趟运输油料的车。后来我们还认识了那趟火车尾车的守车师傅,也是武威人,他把我们带上了尾车烤火,坐车条件也算有了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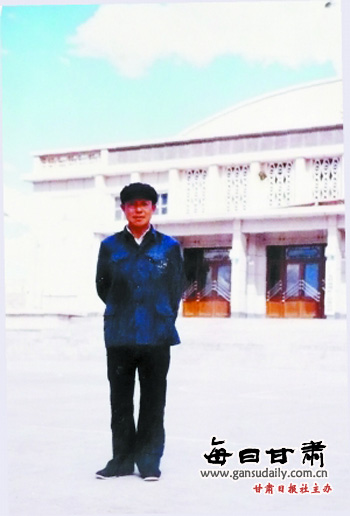 |
在修建完工的老君庙俱乐部前留影
挖地道时遇到难关,从嘉峪关学来了古人的砌砖技术
在玉门,我们基本上不挑活,急难险重的活也一样干。渐渐的我们在玉门油矿上有了名气,再加之武威老乡也多,得到的信息也多。来打工的民工也渐渐多了,已经有60多人了。
当时正是备战备荒的年代,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中,各地都开始挖地道了,我们也接了挖地道的活。挖地道的考核和挖沟的考核是一样的。
说实话,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挖地道和现在挖地道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挖地道打隧洞,基本上有钢筋混凝土。我们的地道,全部是砖砌的,这就有相当的难度。挖直洞时,并没有多少难度,不外乎是木料支撑,然后砌上砖头。这个活简单,也容易出活,大家干得很起劲。
很快,我们就遇到了难题,地道的十字路口和转弯处怎么办?我们那时并没有接触比较复杂的砖砌技术,虽说在农村干过砌墙之类的活,但相对简单,那属于直线工程。十字路口和转弯处的砌砖工程难住了我们。这种地方砖怎么走,谁也没有办法……
一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向玉门油矿的领导建议说,实在不行,可以到嘉峪关看看城门的拱门的砖的走向,或许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当时,嘉峪关是某单位的炸药库,一般人进不去。玉门油矿派了一辆大卡车,还出具介绍信,让专人带我们进了嘉峪关城楼……我们仔细观察了古人的砌砖技术,还绘制了不少图样。回去后,基本上掌握了地道砌砖的技术。
我们这一帮人的活干得又快又好,玉门油矿的领导大为满意,一次大会上还专门表扬了我们,特地给我们奖了两只羊。
谁知我们从冷库中领了两只羊后,却引来了天大的麻烦。工期紧张,我们拿着羊没有去厨房,就直接来到了地道施工现场。几个路人看到我们拿着羊,悄悄告给了工宣队。工宣队闻听这个消息后,二话不说,就打着检查工程的旗号来检查我们。在现场发现两只羊,工宣队让我们拿出凭据来,羊是奖励的咋会有凭据,我们自然拿不出来购买的凭据。
于是,工宣队的人当场就把我们几个人带走关了起来。工地上的民工四处找人,最后玉门油矿的党委副书记傅万祯知道了,赶紧派秘书过去说明情况。工宣队最后只得说声“误会”将我们释放。
接了一个大活,找了河北的瓦工助阵,对方竟然是修过人民大会堂的师傅
干了三年多,我们这伙人的名气渐渐大了。一天,在玉门百货公司的那位女同学说,贸易公司要修三排宿舍,每排10间,都是起脊瓦房,问我们愿不愿意干。我们打工在外,有活干就不错了,哪里还有挑选的余地。我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
说实话,心里没底,盖这样的起脊瓦房的确还是头一回,这和农村盖的土坯房可是两个概念。既然接下了就要干好,不能打退堂鼓。再说了价钱给得也不错,一个平方13元,出来打工不就为赚钱嘛。
正好,武威县食品公司孙主任的哥哥孙宝森是河北保定一个建筑公司的高级瓦工,孙宝森到武威投奔弟弟,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活。这位孙师傅,可算是及时雨,我立即决定拜他为师。
原来,孙宝森在抗战时,曾被日本人抓去修过碉堡,后来又被骗到日本当过劳工。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修建工作。孙宝森师傅的技术自然不错,他又从老家叫来了7位瓦工,这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们一边干,一边跟孙师傅学技术,整个工地就成了我们的实习场,等这项工程结束后,我们也学了不少技术,成了许多人以后安身立命的本领。
我们这伙打工者,就是依靠着勤奋好学肯吃苦,不少人后来干出了名堂,有的后来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