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创作门外谈之一
(原创:应学俊)
最近流传一种小说创作理论,概括一下叫做“把A当B来写”。具体说来就是“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把自己当罪人来写”。为了强化对事不对人,为了仅仅是探讨一种小说创作思想与实践的关系而不旁骛,所以笔者不提及这一理论的发明者和践行者,以免分散注意力。
笔者不是写小说的,这里仅从哲理的层面做点探讨,算是“门外谈”了。如有啥不对,姑妄看之,也欢迎讨论。
最初听到这理论是在去年。2011年8月26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后举办中外媒体见面会,这位获奖小说作家似乎沉痛而颇有担当地说:“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应该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社会,关注他人,批判现实,所以我提出了一个观念,要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当某种社会灾难或浩劫出现的时候,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必须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值得批评的事情。《蛙》就是一部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认为《蛙》在我11部长篇小说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见2011.8.26.人民网)
然而笔者对上述所谓创作思想有一些不敢苟同的想法。它毕竟关乎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一)
“文学即人学”,这是不错的(当然“人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少触及政治,多揭示人性自然无可厚非。基于人性都有善恶两面的客观前提(正如这位作家所说“人都有七情六欲,好人有阴险的一面,坏人也会有善良的一面”)——这位作家发明了“把A当B来写”的创作理论,似乎很辨证,很深刻,跳出了脸谱化的陈腐窠臼,而且发展到高级阶段——“要把自己当罪人来写”,如此严于解剖自己简直胜于鲁迅、卢梭,这就几乎要令人感动了。但笔者以为这恰恰是失之偏颇的。
其一,它抹杀了这个世界上确有相对意义的“好人”、“坏人”之分这一客观事实,如此看待世界很容易陷入好坏、是非模糊价值混乱的泥沼,既容易使读者糊涂,作家自己也往往进退维谷难以自拔。以“把好人当坏人写”为例——如实写出“好人”亦有的七情六欲以及他的缺点、局限性等,与把他“当坏人写”是不同意义的概念,是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位作家在阐述上述理论时并未加任何限制和前提,而是直言“应该”——于是我们不禁想到,是否“应该”把焦裕禄一类好人当“坏人”来写,专找他们的阴暗面?是否“应该”将《巴黎圣母院》中阴毒的克洛德神父当“好人”来写,专找他“良善”的一面?可问题是,我们即使写出类似焦裕禄一类好人“不光彩”的一面,可大约还是否认不了他们是好人……
其二,“把A当B来写”难避主观意志先导先决以及“主题先行”之嫌,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引导下容易扭曲客观事实和人物性格。试想,当我们描写一个人物命运时,头脑中先定下把他“当什么来写”,而不是从这个人和这类人的客观实际来分析考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抓住实质,这会导致创作中怎样的情况发生呢?应当无须细述。
笔者以为,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尊重生活的真实,洞悉人物、现象的本质,写好人不必刻意“高大全”,写坏人不必全部“假丑恶”。人性尽管皆有善恶两面,但当一个人身上是恶为主导时,尽管他也有良善的一面,他的所作所为使他总体上属于恶人一类;当一个人身上是善为主导时,尽管他也会有不光彩的言行,但他客观上自然是良善为主的好人。正如俗语说:有缺点的鹰还是鹰,有优点的苍蝇终究是苍蝇。是非善恶还是有所区分的。而对更多说不上好人、坏人的“中间型”普通人,我们自然无须将其归类,抓住具体实质如实道来才是可取的。
明明是有缺点的好人、普通人,硬要主观上把他“当罪人、坏人来写”,这可以吗?明明是恶为主导的恶人,只因为他也有一些良善之处,于是就主观上“把坏人当好人来写”,这难道不是一种扭曲吗?A就是A,人为“把A当B来写”恐怕靠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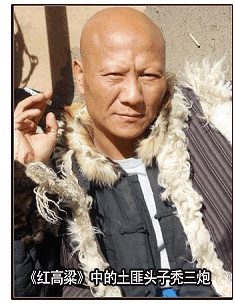 如小说《红高粱》中,面对日寇入侵也同样危及自身时,土匪头子参加了抗日斗争,最后被日本鬼子残忍杀害了,他没有低头求饶;就此而言,这无疑是值得肯定值得书写;但这并无法掩盖和抹杀其曾经对许多无辜黎民百姓抢劫虐杀造成他人家破人亡的罪恶和残忍;他参加了抗日并不等于他的罪恶就不存在且无须鞭挞了—— 一个土匪头子最后也参加了抗日斗争,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过,这说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说明爱祖国天然正义和合理,这说明有的恶人并非毫无良善之处,这便是真实的“恶人”——反映社会的真实和事件的本质即可,有必要刻意“把坏人当好人来写”吗?只有这样才显深刻而辩证吗?
如小说《红高粱》中,面对日寇入侵也同样危及自身时,土匪头子参加了抗日斗争,最后被日本鬼子残忍杀害了,他没有低头求饶;就此而言,这无疑是值得肯定值得书写;但这并无法掩盖和抹杀其曾经对许多无辜黎民百姓抢劫虐杀造成他人家破人亡的罪恶和残忍;他参加了抗日并不等于他的罪恶就不存在且无须鞭挞了—— 一个土匪头子最后也参加了抗日斗争,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过,这说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说明爱祖国天然正义和合理,这说明有的恶人并非毫无良善之处,这便是真实的“恶人”——反映社会的真实和事件的本质即可,有必要刻意“把坏人当好人来写”吗?只有这样才显深刻而辩证吗?
如果“把坏人当好人写、把好人当坏人写”并最终“把自己当罪人来写”是一种深刻而杜绝“脸谱化”,是一种正确的创作思想和方法,那么在《巴黎圣母院》中对神父克洛德即所谓“坏人”与吉普赛姑娘艾丝美拉达即所谓“好人”的描写,雨果是否也落入了肤浅和“脸谱化”的窠臼呢?
(二)
芸芸众生,不可能皆为圣人、英雄,我们除去明显的恶人、小人和特别良善之人、英雄式人物,大多还是称不上“高尚”的普通人,他们既不失良善为主的特征,在某些时候也会有明显的懦弱、私心之丑。如按作家自己所说,笔者以为这位作家在德行方面至少属于也许并不“高尚”却占人群大多数的普通人之列吧?如果作家认为因偶有私心陋行就是“很卑鄙”的“罪人”,那么作家是否是在论证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高尚”就等于“卑鄙”“罪人”吗?这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吗?这是不是形而上学?作家对自身有所反思忏悔是可贵的,但有必要刻意“把自己当罪人来写”吗?以这样的思想指导创作,会不会扭曲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命运呢?难怪有的读者读了这位作家的某些作品感到“茫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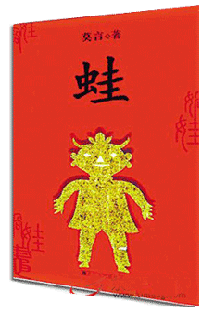 实事求是地说,这位作家的大多作品客观上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由于人为灾难、浩劫给百姓苍生带来的痛苦和悲惨,有些隐喻细想也颇辛辣,不论用了怎样“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这都是很有价值的和值得称道的。他的作品无疑好过他对自己创作思想带有明显偏颇的阐释。
实事求是地说,这位作家的大多作品客观上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由于人为灾难、浩劫给百姓苍生带来的痛苦和悲惨,有些隐喻细想也颇辛辣,不论用了怎样“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这都是很有价值的和值得称道的。他的作品无疑好过他对自己创作思想带有明显偏颇的阐释。
计生国策不能厚非或无可厚非,“姑姑”这么好的人几乎也无法责难她,计生政策实施过程中那些不人道的漠视生命的恶行究竟是谁之过?小说怎么写?——“把自己当罪人写”!作家说“《蛙》就是一部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
其实,“姑姑”和作家这类人虽非英雄、圣人,但也不可能是“罪人”,何况“姑姑”原本是那样善良!作家主观上或潜意识里对于造成“姑姑”这样既是受害者又成为被动害人者的悲剧根源,挖掘得已经基本到位了——《蛙》中作为小说的叙述人“蝌蚪”直言:她“太听话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认真了”——这不是悲剧的根源吗?继续挖下去,是什么把“好人”异化为客观上的“恶人”?是什么使一个个原本有头脑能思考的独立的人异化为类似一部机器上没有思想甚至几近失去人性的“螺丝钉”?这恰恰是需要深刻反思的普遍现象。可惜作者只愿意看到一面,把受害者“当罪人来写”,似乎这样便更“深刻”,更“合理”。
在“把自己当罪人写”的思想指导下,作家面对媒体曾举例,坦言他在执行计生政策的过程中也有“罪过”——那就是违心地、冠冕堂皇地动员妻子按政策要求去把超计划的孩子“做掉”。作家说,其实他是迫于压力怕影响自己往上提升的仕途,到现在想到此还有深深的隐痛,“到了晚年,我想起来感觉自己很卑鄙啊!”且作家在电视上有意把“卑鄙”二字说得很重。看来在这位作家的逻辑中,不高尚不英雄就等同“卑鄙”——诚如是,那作家骂的就不仅仅是自己,而国人皆为“卑鄙”之人了。正因为作家并非从生活实际出发而是刻意“把自己(包括“姑姑”)当罪人来写”,所以作家在媒体上解读《蛙》的主题时,总使人感到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不知所云……
这位作家的创作思想符合生活的真实和逻辑吗?一味鼓吹这样基督教式的个人“反思”和忏悔,能使芸芸众生都成为圣女贞德或张志新、李九莲、王容芬那样以死反抗邪恶的英雄、圣人吗?把作家和“姑姑”这样一类芸芸众生“当罪人来写”除了施害者的罪魁感到苟且的欣慰,有助于人类的救赎和社会的真正进步吗?“姑姑”人性异化的根源真的是自身因素使然吗?
正如山东师范大学周志雄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姑姑’的人生命运和精神心理变化无疑是时代对个人的压迫所致,在大时代中,个人不过是一枝随风的芦苇,‘姑姑’是时代观念的受害者,是历史运动的受害者。”姑姑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姑姑’的精神矛盾分裂症是时代造成的,它隐喻了历史现实对个人的巨大伤害。”把“姑姑”和作家自己“当罪人来写”是不合事理和逻辑的。因此,笔者认为《蛙》应当在启迪我们个人反思和忏悔的同时,还应启迪读者反思给这个社会造成悲剧和灾难的根本原因,避免以后的“灾难”把更多如“姑姑”这样的好人异化为恶人——作家如能这样客观全面地看待反思和忏悔,就不仅有助于塑造符合逻辑的典型文学形象,有助于每个人灵魂的救赎,而且真正有助于社会的纠错和进步。只有在好的大体合理的社会中,好人才会越来越多。仅靠像“姑姑”一类芸芸众生去时时自我反思和忏悔,除了能获得自我心灵的慰籍和升华,对社会进步仍然是回天乏力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再有灾难、浩劫降临,他们依然会成为善良的只会“解剖”和忏悔自己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反思作家所说的“别人、外界的责任”——分析造成社会悲剧的重要源头,“姑姑”只能捏上许多泥人来表示这对自己“罪过”的忏悔而不可能思考其它——至于作家这里的“别人、外界”所指为何,笔者以为是无须说明的了。
(三)
中国实在经历了太多人为灾难尤其是历时10年的“文革”浩劫,的确需要反思和忏悔,也需要宽恕与和解。但文化学者朱大可教授对此有过比较全面而精炼的阐述:对施害者(包括既是受害者同时又加害过他人的),推动忏悔的前提是认知,道歉补偿是忏悔的外在表达;宽恕是受害者对忏悔的良善回应;清算是针对拒悔者的必要程序;和解则是公民社会的最高本性;共同追问和制度矫正,是新罪预防的最后保障”。这是很具有逻辑性的对于忏悔机制建立的阐述。
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是不错的,但就社会灾难和浩劫而言,绝不应仅仅局限与此,施害者亦即作家所说之“别人、外界”更应反思和忏悔,因为他们是制造全社会积灾难的罪魁,他们的反思和忏悔才会带动全社会的反思和忏悔。反思自我并不等于人人应当为灾难负责,任何人只能负属于他的该负之责,而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罪错人人有份”。对拒绝认知错误(亦即反思和忏悔、道歉)者一味讲“宽容”就无异于助纣为虐,迎来的将是有权制造灾难的强势集团施害者重新导演使生灵涂炭的历史悲剧,这绝对无助于人性的救赎和社会进步的实现。
“文学即人学”,但人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一个好的大体合理的社会中,如《蛙》中“姑姑”这样大多数的好人才会有符合逻辑和情理的好人的命运,更多的好人才不会被动地异化。
只要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创作思想就必然指导创作实践。笔者以为,我们并不要求作家必须成为有社会担当的英勇斗士,文学可以纯粹一些——但是,A只能当A来写,是A就是A,不应人为地将其变成B。作家应遵从生活和艺术的真实。在启迪心灵自我救赎的同时,直面异化人性的根源所在。否则我们还要文学干啥?——人人皆做基督徒足矣!如总是人为地“把A当B来写”,扭曲生活、失之偏颇从而误导读者价值取舍也就在所难免了。
实话实说,本文论及这位作家的作品其实比他对自己创作思想的阐述和某些行为要高明几倍或十几倍。然听他阐述这些理论的人恐怕又大大多于真正读他小说的人,所以笔者不得不议论一下。非小说作家的“门外谈”,仅供参考。
2012.10.26.
【参考文献】
1、莫言作品《蛙》《生死疲劳》《红高粱》等
2、【视频资料】该作家相关访谈视频片段
2、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周志雄:《历史之痛与忏悔之思》
3、朱大可:《无比艰难的道歉——关于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