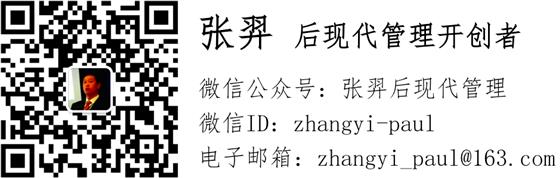张羿:管理学是巨变时代的真正灯塔
2004年4月,我的第一部管理学著作《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问世。虽然该书只是后现代管理的宣言,尚未完全深入地构建起后现代管理大厦,但因其突出的跨学科视角和思想深度,得到了管理界权威的认可。中央党校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原主任、时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孙钱章教授看到书稿后,力荐我出席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发起人董新保教授等知名学者则热情地为我的新书写评语。董新保教授是剑桥大学克拉霍学院终身成员,当年正是在他的邀请下,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才出面创立清华经管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的。
《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初稿完成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教授对个别章节提出了修改建议。而该书出版之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诸多媒体追踪报道,主流财经媒体纷纷约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全程转载了该书节选。其后,很多大学把该书列为博士研究生参考文献,一些学者的论文也频频引用该书观点。2004年7月,在由瑞典哥德堡大学主办的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上,我的主题演讲《现代企业的终结与后现代企业的兴起》引起了来自全球各大商学院知名管理学家的关注。
回国后,接到更多财经媒体的约稿,也零星接受了包括时任《经理人》杂志高级编辑、现为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撰稿人的罗天昊和《数字商业时代》主笔金错刀等著名财经专家的采访。但我还是谢绝了大多数媒体的约稿,一来工作紧张,闲暇时间不多;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还存在很多欠缺,不仅对后现代管理体系的构筑尚欠火候,也缺少足够的全球企业实践佐证,后现代管理还未到真正抛头露面的时间。其后,虽然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先生等展开过有关后现代管理的公开辩论,在业界引起过一定的反响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埋头于企业实践和对后现代管理的进一步研究了。
2005年夏天,时任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的齐善鸿教授来上海开会期间约我交流。齐善鸿教授认为,后现代管理是未来全球企业管理变革的必然方向,这是一项真正开创性的研究,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管理学的突破性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齐善鸿教授还与我探讨了将来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管理学对我从来不是书斋式研究,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管理实践者。自1997年从国家建设部主管的《中华锦绣》画报社辞职进入企业工作后,二十年来,我经历了从经理人到创业者等多重角色的转换,跨越了高科技、管理咨询、商业地产和互联网等多个行业,始终处于管理实践的第一线,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者。从《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出版至今已经12年有余,期间,除了2007年因痛感台湾曾仕强先生的中国式管理对中国企业实践具有太多误导,而出版《中国式管理批判》外,我没有再写其他管理著作,并暂停了与管理界和媒体界的接触。我想沉下来,在实践中对后现代管理进行更全面而深入的体验、观察与研究,以期在适当的时候再度推出一本成熟的、能够对全球企业实践具有切实指导价值的开创性著作。这就是今天的《管理救赎:超文化企业缔造》。
这是一个全球企业都需要管理救赎的时代。当代思想界创新乏力,管理学的建设更落入急功近利的工具主义泥潭之中。在这样的巨变时代,我们尤其需要象德鲁克那样高度跨学科又极具实践性的管理学创新。在哲学终结的背景下,管理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建设性和引领性的人文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东西方学者众说纷纭而鲜有突破,导致大部分思想者都陷入怨妇式争辩的陷阱。这使我对当代思想界敬而远之。虽然在这12年间,我也曾与中国思想界有所接触,其中还出席了第一届海安523中国当代艺术思想论坛,发表了《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主题演讲,引起艺术圈的热议。但最终,我还是怀着对思想界清谈之风的厌倦而回到管理学的大地上。当然,我从来未曾离开过管理。
管理学让我感到踏实,它是巨变时代的真正灯塔。正如王阳明所倡导的,若没有真正的实践,就不会有真正的知识,知行合一才能构筑坚实的知识大厦。而管理学尤其如此。怀着对国家、民族、时代和人类的深沉使命,管理学让我找回了真正的大陆。管理学是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学、历史学、领导学、传播学等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集合体,它所需要的功力比任何一门人文学科都要深厚,同时更须艰苦卓绝的实践磨砺。从某种意义上,管理学才是真正的人学,而不是文学和艺术。文学艺术在追求人性的过程中,很容易走上扭曲人性的歧途。而管理学更能使人性回归到真实的大地上。
在坚硬的大地上,我们首先是一个劳动者。若任何学科不能有助于我们成为一个更合格的劳动者,而是导致我们与现实格格不入,这门学科就注定是失败的。管理学并不是一门功利主义学科,它是真正伟大并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人学。我并不否定其他人文学科的作用和重要性,恰恰相反,正是其他人文学科滋养了我,使我能够以不同的材料构筑管理学大厦。我想强调的是,在一个相对主义蔓延的时代,我们不如先通过管理实践而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这样才够分量去从事任何学科的建设。否则,我们会给这个原本沉重的世界增添太多的包袱。我不是批评别人,而是与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共勉。
也许谈太多理想会让处于残酷竞争现实中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感到虚夸,那就让我们回到管理实践!事实上,本书绝对是实践性最强的管理思想体系。因为本人是一个管理实践者,而且一直痛恨各个领域的清谈现象。
虽然本书是我对后现代管理历时二十年的研究总结,但它一定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作为对现代管理体系的全面颠覆和对后现代管理体系的全新缔造,本书今后仍须不断提升。这有赖于企业界、管理学界各位同仁的指点,社会各界朋友和读者的批评指正。期待各方人士共同推动本书及后现代管理体系的完善,这对于整个世界都意义非凡。
是为序。
张 羿
2017年1月1日于上海
作者简介
张羿,后现代管理开创者,著名管理学家,企业家。现为上海信约管理创新咨询公司董事长。曾任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委会秘书长;曾受邀为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在职研究生班和政商精英班导师;曾任《商界评论》、《管理学家》、《中国新时代》等媒体专栏作家或特约撰稿人。
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2004年)、《中国式管理批判》(2007年),系后现代管理开创者和中国式管理批判代表。多次应邀在世界顶级管理论坛、著名大学管理学院等发表后现代管理主题演讲,均引起强烈反响。著作被多所高校列为博士研究生重要参考文献,为众多管理学专业论文所引用;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企业家》、《经理人》、新浪财经等报道或转载。
曾在中国管理传播网与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仕强展开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在博客中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展开后现代商业精神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接受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撰稿人的罗天昊和《数字商业时代》主笔金错刀等知名财经专家专访。曾因《万科与世界级企业的真正差距》一文被《中国企业家》杂志转载引发强烈反响,该文在十年前就指出万科治理结构的隐患,间接预警了“宝万之争”。
2004年7月,应邀出席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发表《现代企业的终结与后现代企业的兴起》主题学术报告,引起国际管理界强烈关注。《管理救赎:超文化企业缔造》系张羿第三部划时代管理学力作。
张羿历经二十年企业实践,具有从记者到经理人到创业者的丰富从业过程,同时身兼思想家、管理学家和艺术批评家等多重学术背景。其管理学著作视野开阔,理论与实践并重,是中国本土第一位具有世界级高度的管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