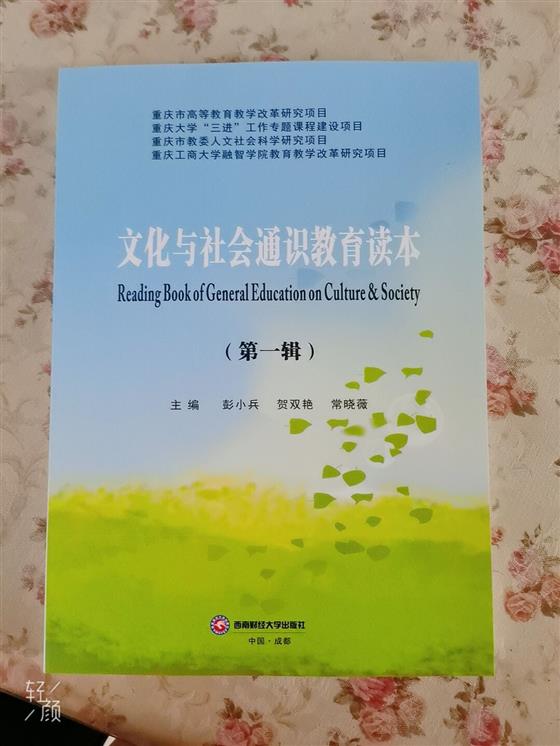爱与公义:公益慈善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信仰解释
1.爱的社群纽带
公益慈善促进社会发展,可以通过“爱”的多种形式展示其作为社群纽带的意义。著名歌手韦唯演唱的那首《爱的奉献》曾经响彻大江南北,“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那句歌词,曾感动了一代人,直到现在仍被无数人传诵,其内在道理是因为爱本身揭示了一种社群意义和价值。爱,可以给人温暖与力量,爱,可以融化人际间的隔阂,弥合社会的对立分化。公益慈善的本质就是传递一种爱,因此公益慈善事业本质上就是爱的事业,它在现代社会中的社群纽带作用越来越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爱”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普遍而又复杂的概念。社会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将爱定义为给予和分享。尽管有关“爱”的界定比较复杂,但其核心内涵不变,“爱”天生地具有群体性的意涵(孙艳萍,2014)。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在“光辉灿烂”三部曲(The Radiant Trilogy,1987-1991)中以“爱”的普世价值来对抗异化的、碎片化的现代生活,坚持用情感来补充现代理性世界,建构起现代社群道德,并传递给人们这样一个温馨的信息:“爱”是人类形成亲密无间、相互信任的关系的纽带;“爱”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守望相助的伦理团结的纽带。
(1)自爱。“爱”是一种美德。爱邻舍、爱他人,也要爱自己,这就是“自爱”(self-love),是人类美德的根源。“自爱”不是“利己”,而是内在创造力的表现,是爱别人的一种表现,因为自己和他人都是美好、平等的存在,都值得每个人去爱、去珍惜。以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为代表的哲学家不仅肯定“自爱”,而且从不同角度指出了“自爱”的社群意义。例如,卢梭在《爱弥儿:论教育》(Emile, or On Education,1762)中区分并肯定了爱自己这种关心自己、渴望自己幸福的人类最原始的情感和爱他人这种随着群居生活状态带来的持久、稳定的社会交往;在《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1956)中弗洛姆都主张爱他人和爱自己都是美德,“爱我同爱另一个生命是紧密相连的”,并把“自爱”看作爱的能力的体现、爱的起点。《圣经》中“爱人如已”的教导更展示了人类应该向往和被驱动去做的一个完整的爱的架构,即对自己的完整的、独特的尊重,爱自己,理解自己,与尊重、爱和谅解别人一样,是完整不可分割的。这种对“自爱”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把“自爱”与“爱人如己”这种社群意识、社群精神联结起来了。真正的自爱是内在创造力的表现,因为对自己成长过程的确认、认同,会强化一个人爱他人的能力。只有自爱的人才有能力去爱别人,才能在一个群体中让他人感到爱的存在。
那么,什么是自爱呢?可以肯定的是,“自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自爱不是自私,“自爱”不等于把追求个人欲望和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与自私的损人利己、取小利失大利不同,自爱是建立在与他人和社会和谐共生的基础上,目标是共赢,这就是爱的社群意义。此外,自爱者绝不妄自尊大、自夸自傲和妄自菲薄、自暴自弃。相反,自爱是寻求内心的平静——人内心深处的坦然,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抱以温和宽容的态度。自爱的内涵及价值包括:1)承认自己的不完美、缺陷和不足,进而愿意谦卑下来;2)关心自己的幸福和正当利益,肯定自己的价值,把自己看成是是有价值的、宝贵的,支持去实现自我的发展;3)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当然也包括不能加害于自己,自爱是爱护自己的身体,珍惜自己的名誉;4)有信心、有喜乐和有盼望;5)为自己预备时间,锻炼自己的身体和建造自己的心灵;6)重塑对他人的信任,改变不信任,允许爱进驻(let love in)。此外,Eugene Gendlin博士在《聚焦姿态》一文中也总结了真正自爱的三个方面:其一,温柔地对待自己,要友好地对待自己内心的感受。有时感觉伤心、受伤或者害怕是很正常的。这是力量的象征,而不是懦弱的表现,注重这些感觉,友好地对待它们。其二,正视我们的经历,爱自己就是允许我们去体现自己的感受。其三,拥抱未知的智慧,因为我们内在的感觉是模糊不清的,需要暂停下来,为这些模糊不清的事情腾些空间,耐心地去探索那些模糊不清的感觉。
(2)亲情。亲情是每个人最宝贵的感情。亲情给人以群体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由婚姻、血缘和家庭衍生的各种亲情关系是情感的主要寄托,也反映了人类对亲情的向往。在患难、困境中,人们可以用亲情抵御生活的磨难,在充满艰辛的生活中坚强成长;人们也会想方设法地保护好亲人和家园不受侮辱和侵犯,是因为人们相信亲情能赋予人坚守自我的强大内心,不被战争、灾难、困境、难处所吞噬,不对生活失去信心和希望。2020年,面对突发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肆虐,亲情是燃起希望的火把、支柱,而亲人的不幸离别,对一个具体的家庭来说犹如希望的湮灭。
因此,以亲情为纽带的家庭的爱乃是一种博大无私、超脱于利欲熏心的怜悯,是授予、牺牲、仁爱。作为一种物质、心理、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存在,以家为中心的亲情和生命真谛,具有极为重要的社群意义。这种关系的推演,可以成为公益慈善的基础、最初起源和表现形式,如关注对方的需要,学会真诚地付出,尊重对方的独立性,认识到他们和我们一样有自身的需求、会因为无法实现需求而遭到挫折,在沟通中了解和倾听他们的需要。当然,正如我们不会纵容亲人犯错一样,在社群中关注他人的需要不意味着纵容,而是支持对方通过积极、健康的方式来实现自我。
(3)友情。友情是家庭之外的社群中最重要的情感和关系。公元前326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其论著《政治学》(Politics)中具体阐述了群体生活的重要性,认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通过城邦的存在说明了群体生活是人的本性,也通过人的本性论证了城邦的合理性。亚里士多德一切以城邦为重的政治学思想,映射到伦理学中就是倡导社会成员之间的友爱。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思想,实际上也揭示了社群主义当中的友爱故事。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友情之爱或者说友爱,对于个体和共同生活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人要跨越疏离之樊篱、拥有丰富多彩社群生活的重要途径。此外,亚里士多德用“友爱”是一种非情绪的理性化情感,所强调的是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2007)所评价的“那种无私的帮助、共同的分享和相互的依存”以及“一种罕见的均衡与和谐”。这是友谊的本质:理性,交流,慰藉,认同,尊重,患难与共。同时,友爱还是一种行动。友情的本质表现在为朋友而行动的过程中,即人追逐友谊不能只从记忆或想象中去寻找意义,而是要去亲身体验,主动去为友人和自己思考生存、现实、人际关系、社会实质等问题。真正的友情是基于善的友爱,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培养出来的,社群生活是友情的承载体,只有这样友情才能实际地存在。
那么,友情从何而来呢?一方面,通过共同学习的经历、共同奋斗的生活、共同信仰的真理,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从而结下友谊;另一方面,不同教养、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人之间也可以通过聚会这种公共空间,聚集在一起各抒已见,去交流和传递各种迥异的生活经历和心得体会,让各种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碰撞交汇,人们集体性地感受历史和现实,从而逐渐形成个体间的友爱关系和群体性的集体意识。
(4)神爱。在基督教的信仰中,“神爱”是神对世人的爱,一种完全无私无我的“牺牲的爱”,是解决现实世界里各种社会问题的“宇宙的钥匙”。北美殖民地早期马塞诸塞总督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曾经讲过一句震撼人心的话:通过成功地将他们的个人品性与集体的努力奠基于《圣经》中爱的理念上,他们就必然能建立起一座繁荣、强盛、为万人所敬仰的“山巅之城”。这里,神是基督教信仰爱的基础、出发点和终点,这样一种爱具有神圣性和命令性,是一种先于天地规定的使命感。正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驱使特蕾莎修女梦想并毕生追求这种没有阶级差别、平等的和公义的社会,在特蕾莎修女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勇气和努力,这是神爱精神与有信仰的人建构社群的努力的结合,成为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道德力量,进而糅合在自爱、母爱、亲情、友情等形式当中。
综上,爱是内心的一种感受、一种自我救赎的体验和一种超越现实物质束缚的人格。在当今全球化日渐深入、世界却又泛起层出不穷、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矛盾中,在纷纷攘攘、转瞬即逝的,唯有公益慈善中的“爱”,才是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找到群体归属感的精神核心。这是爱的社群功能,也是透过公益慈善促进社会发展的桥梁。必须建立起“以兄弟间情感的纽带”,即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于1630年春天在阿尔贝拉号(Arbella)远航帆船上的一次平信布道演讲上所阐释的:“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温顺、柔和、耐心与慷慨一起启动一项熟悉的事业。我们必须在对方之中喜乐,令对方的情况与自己相同,同悲同喜、同工同受,在工作中时时念及我们的使命与共同体。”这是现代公益慈善的真谛。
2.社会公义的普遍追求
公益慈善事业为什么会存在,以及为什么需要存在?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从公益慈善服务供给的个体或自身角度来看,企业和个人(家庭)的公益慈善捐赠有心理和功能上的双重作用。其一,心理上的原因:“成就需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把人的需求依次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其中参与公益慈善活动、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是满足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重要途径。其二,功能上的原因:公共关系和社交手段。公共关系是指企业利用自己的资源影响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行为,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行业组织、媒体、意见领袖、社会公众、供应商、代理商、客户、股东、员工等,参与慈善公益活动是提升政府、媒体、客户和社会公众对企业品牌的知晓度、偏爱度、信任度的重要公关和社交方式。当企业或个人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做出贡献时,也会从社会得到各种性质的回报。而从公益慈善服务需求的角度来看,以慈善捐赠为核心的公益慈善事业,是消弭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和事实上的财富不平等乃至社会不公平问题的最佳“社会润滑剂”。公益慈善业已经成为国际通行的企业文化色彩,能给企业和企业家带来巨大的诚信和市场。
但对于“公益慈善何以会存在以及为什么需要存在”的回答也可以从社会的角度给出解释,即出于正义、公义与怜悯的需要。如果遵从社会视角的解释,这就意味着,更好地了解公益慈善事业,还需要更准确地把握正义、公义等概念,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公义。
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人类在乎正义或公义吗?在动物世界里,母螳螂为了繁衍后代会吃掉公螳螂;一头熊猫生下双胞胎,她可以丢掉一个而只抚养另一个。那么人类呢?现实的观察是,人类社会也到处有不断地牺牲他人利益的现象。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一个人越弱小就越容易被欺负;且这种事情不仅发生在个人层面,也发生在家族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所有的社会文明中都发生过,导致不公义的事,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问题是,这些现象,动物那样做,我们没有谁会去谴责;但人类做了同样的事,人们可能会说这是错误的、不公正的。也就是说,人类很在乎人类自己的非正义与不公义现象。
为什么人类这么在乎公义呢?似乎按照世俗的法则,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个现象,只能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圣经》和犹太教、基督教的观念里,人与其他动物是有分别的,因为在犹太-基督教观念里,乃是人有上帝的形象。人是按照上帝对善恶的定义来掌管世界。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有自由的权利、应有的尊严和公平的对待。
在犹太-基督教的观念里,正义是一种道德标准,是人与人之间正确的关系。正义,就是把人看着有上帝的形象来对待,给他们应得的尊严,这尊严是上帝所赋予的。而在希伯来语中,公义,可以是指一种报应性公义,好比是人偷了东西,就应当承受后果。但公义大部分时候指的是修复式公义,意味着要向前一步,主动寻找被欺压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有人称这为慈善事业,即Charity的词源。甚至远不止如此,犹太——基督教观念里的公义,意味着我们要站出来,支持弱势群体,改变社会结构,避免不公义的发生,这就是公益产生,也是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精神(伦理)源头,更是“公益慈善”要紧密关联到“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关注社会发展是公益慈善事业之内在的、本质的要求。因此,在传统上受基督教深刻影响的西方国家社会中,公义和正义指的是一种彻底的、无私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如此,即公益慈善不仅是社会个体行为,更是一种追求公义的治国理念和生命价值。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济贫帮困等“慈心为人,善举济世”的优良传统,且从公益慈善文化的利他精神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利他精神,而且这种利他精神不仅仅局限在现代人所理解的社会个体的公益慈善行为上,还构成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基本治理理念。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筑了从社会个体行为到整个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思想、伦理架构;《孟子∙梁惠王上》中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礼运》说,在大同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实际上表明中国许多传统文化思想均认可和要求抚孤托幼、养老济贫乃至残疾人保障等属于公益慈善的事业也是个人和国家的共同责任,是一种社会公义。以公益慈善精神要求执政者和每一个家庭、族群、个体,是中国公益慈善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社区建设与社会治理内涵。因此,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利他的公益慈善精神既是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涵,也是心存怜悯、追求社会公义等生命终极价值的奥妙所在。
进一步地,按公义判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以下的描述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本质内涵。那就是,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要为不能自辩的人开口说话,为困苦和穷乏的伸冤;要施行公平和公义,就是解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者的手,为受欺压的人伸冤;不可虐待或以强暴对待寄居的、孤儿和寡妇;赐食物给饥饿的人,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遇见做客旅的、流浪的,给他住;看见赤身露体的,给他穿;有生病了的,去看顾他;有落在监里的,去探望他;使被囚的人得自由,却使恶人的行动挫败。
不幸的是,这个世界,有人故意做不公义的事,其他人甚至会把这种不公的社会结构看作理所当然,并从中获利。更可悲的是,历史告诉我们,这种不公还会历史循环:当被欺压的人获得权力之后,他们往往会成为欺压者。所以,无论是主动、或被动,甚至是无意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参与在不公义当中。且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于是,面对人类持续不断的不公义,我们就号召要去行公义,而公益慈善事业就是一种行义的方式、途径。公益慈善,不止包含了一种新的身份,更是改变他们生命、并推动他们以惊人的方式去行动的一种能力、一种途径(而不需要像古代侠客一样去替天行道),去为其他人寻求正直、公义——这是一种颠覆的生活方式,且并不总是简单的、轻松的,而是要求人勇敢地把他人的问题变成自己的问题,要求人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也就是所谓的爱人如己、爱邻舍,或牺牲的爱。因此,爱心不单是一种情感,更是一个行动,一种态度,是一个人有了新生命之后的产物,爱是为着他人的好处而决定去行。
(摘自:彭小兵,贺双艳,常晓薇主编的教材《文化与社会通识教育读本》(第一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