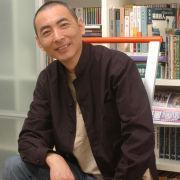窗外飘飞着小雪,就像是一片片小小的白色粉沫纷纷扬扬地飘洒着。大地并没有被白雪彻底覆盖,从高楼俯瞰,屋顶与地面依然裸露出乌色的斑迹,在白雪的映衬下更显丑陋。
很少有人说不喜欢雪,每当雪花飘落时我总会在匆匆走过的路上脸上看到一丝欣喜和愉悦,甚至微笑,这是难得的,国人的表情麻木、冷漠的时间太久了,偶尔一见欣慰的面孔是让人快乐的。
只是这场雪姗姗来迟,它在一整个狂风呼啸的冬季隐身不见,在那个萧瑟的寒冬时节我一次次地仰望着长空,渴望天降大雪,能让我们在雪地上撒一回欢,能让我们迎着那漫天飞扬的大雪尽情地放歌一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