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在学院的信箱中收到了陈力丹老师与他的博士生陈秀云老师合著的《写给中学生的新闻学》,感到非常新鲜:在我们大学讲授的新闻学,“写给中学生”是可能的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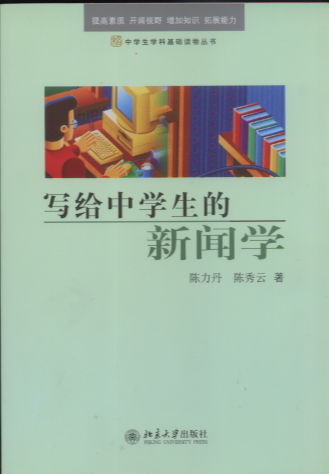
这薄薄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在编排形式和语言上更注意对特定对象的亲和性。比如,它的第四章和第七章都是从某中学的“小记者王小乐”所处的困境开始的——王小乐的一篇关于学校保卫处长抓小偷的报道中,对小偷谴责的话被辅导员老师删掉了。王小乐报道学校火灾的消息没有被校报刊登出来。再比如,它的第二章《只有很少的事实能够成为新闻》,一开始是这样表述的:
“前面我们说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叙述。可是,今天我上学了,其他同学也上学了,这不是刚才发生的事情吗?怎么没有记者来采访,没有传媒报道啊?”
从内容上看,它的体系主要在于传播基本的媒介知识,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和专业操作技能。实际上,在大学,我们并没有叫做“新闻学”的课程或课本,有的只是“新闻理论”、“新闻写作”、“新闻评论”。而这本书只有七章:
一、什么是新闻
二、只有很少的事实能够成为新闻
三、 新闻的真与假
四、 客观:新闻从业的基本准则
五、 怎么写新闻
六、 传媒是个什么样的行业
七、 新闻传播中的“把关”
——显然,既有新闻的基本知识,也包括一些简单的操作性知识。
在回复博友“难道中学也要开设这门课?意义何在?”的问题时,陈力丹老师写道:“意义在于这是出版社商业策划——一本可以赚钱的书,客观上是进行一点新闻学知识的普及。”。
而从表达方面来看,除了语言需要更为浅近、亲和之外,它的困难恐怕还在于:要把语境限定在中学生的知识经验水平上,排除掉在表述新闻学问题时所习惯依赖的大学或成人的知识经验。这一点区别在平时与小孩说时可能不太明显,因为,一方面我们日常对小孩说话都是生活语境的,不涉及更高的知识语境;另一方面,我们对小孩说话时,往往不自觉地“降低语境”,这已经成了我们潜移默化的生活经验。但是,向中学生讲述一门大学的课程或成人的职业规律,则要困难得多,因为依赖于更高的语境——更高的学识和社会经验。
因此,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不免联想起多年前自己曾在北京文津街北京图书馆旧址给一班小学生讲新闻评论时窘境——到了那儿才发现是一班小学生!一种简直不知该如何开口的窘境,因为一开口就想到我说的话可能是他们不理解的:用来解释一个概念的概念本身也需要解释。而任何一个知识的理解,都需要以已经理解了其他相关知识作为前提。比如,你说“新闻不是宣传”,那么,要向中小学生解释宣传恐怕要比解释新闻更困难,除非他们已经知道了“宣传”。
但是,给中学生讲新闻学,不仅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有需要的。
所谓必要,是因为,新闻作为一种普遍的,最为广泛的信息传播,已经走到中学生的世界里了。他们已经不再、不能只看《喜羊羊与灰太狼》那样的童话、卡通版了。新闻影响他们对世界的感知,他们就有必要了解新闻的规律。所谓“有需要的”,就是指,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自觉地走入新闻——各地的小记者、中学生通讯社已经开展了实际的新闻活动。总不能让他们被迫从大学教科书中了解新闻吧?
然而,两位陈老师可能没有想到,写一本给中学生看的新闻学课本,其困难并不在于一位博士生导生和一位副教授与中学生的接近难度,更在于新闻新闻学和新闻这个行业在我们国家中的生存困境和表述困境。就在我前天遇到陈力丹老师,向他表示感谢赠书的时候,陈老师告诉我:在出版时,原书有7000多字被出版社删掉。他把这被删掉的7000多字贴到自己的博客上。 我读过之后感到,中国新闻界的现实处境,也许真的不适宜如实地告诉中学生,因为新闻界的现实和出版界所表现出来的“禁忌标准”,“高于”他们可理解的程度。
实际上,这些被删掉的文字与实说是某种危险的、禁忌的观点,不如说,它们正是中国新闻业的现实。比如这样一段:
“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会说,就在我们家乡,那天出了一件大事儿,烟花爆炸伤了上百人呢,可是传媒没有报道。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样的事儿没有新闻价值?
当然不是。明显地具备新闻价值的事实没有成为新闻,是因为传媒工作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的、文化的原因,还有传媒业务流程中自然追求的省力原则,都会制约传媒对于事实的选择。”
这一段陈述的是中国新闻业的事实。但是,这种事实本身是禁忌的结果,所以,谈到这种事实就成了禁忌。
还有一段:
昨天中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梁保华在南京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及夫人柳纯泽一行,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交谈。[《梁保华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扬子晚报》 2010-11-1]
这是我们在新闻中常常见到的领导外事活动的报道模式:“……某人会见某人一行……宾主进行了亲节友好交谈”,变成了固定化的宣传套路,就不好了。
——这也正是目前中国新闻的常态。但是,你指出这是不对的,在出版社看来,就是对体制的挑战。而且是在中学生面前展示对体制的挑战。它的危险程度有甚于在成人面前表达对体制的挑战。
因此,这虽然是一本“写给中学生的新闻学”,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像“中学物理”那样的一个“中学新闻学”。新闻学,或者是新闻界的处境,就是一个。除非你遮蔽掉真实的部分。“写给中学生的新闻学”被删掉7000字的命运,证明了这一点。
